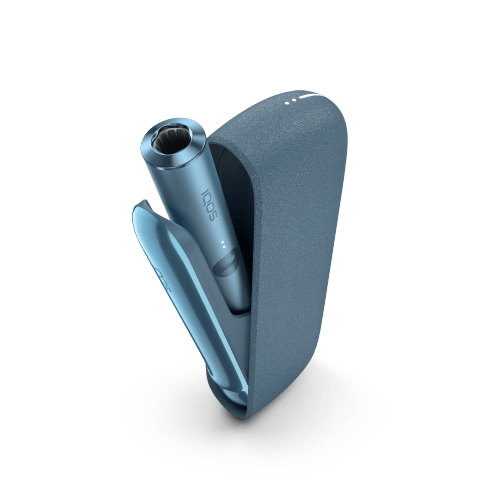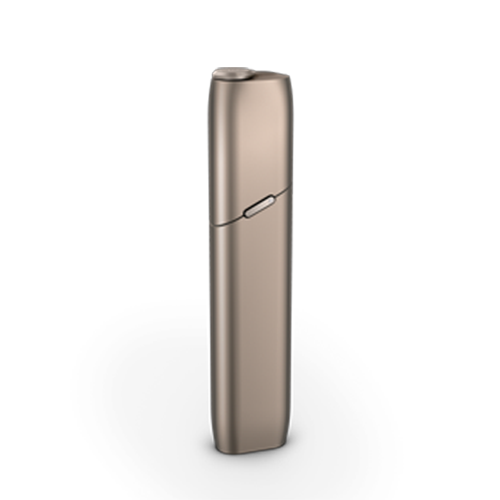我们用四个周末,读了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之基本问题》

计划其实上半年春节时便已列出,微信群也建了,只是未得实行。
“诠释学读书会”读过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读过海德格尔的“纳托普报告”。尤其在“纳托普报告”上,我们花过很多时间。为了读得仔细,王宏健和我分担了此文的重译工作。后来大概用了半年时间才读完。
在这之后,对于接下来再读什么,一直没有确定下来。后来我建议读海德格尔第24卷,也就是这部《现象学之基本问题》。这一提议居然得到微信群内同仁的高票响应。于是便确定下来。
正因为这是我的提议,所以我对读书计划未被正常推动感到歉疚。考虑到时间和效率,读书会到底该怎么进行,一直未有定论。到底是仍然像原来一样,一字一句地读原文,还是换点新花样?
适逢暑假,我便决定在读书会里担纲更重角色,提议搞一个“紧凑读书会”,短时间内把书过一遍。德语世界里有所谓“Kompaktseminar”或“Blockseminar”,大致方式就是,在短短几天内,把一整个学期的课时全部上完。因而,我们的计划就是,在一个月内,分四个周日,把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的四个论题读完。
原本我已然准备自己承担全部四个论题的导读任务。未曾想,读书会的主要主持人王宏健兄瞬间就在群里拉起了一支队伍,妥妥帖帖地为每个论题安排了两位领读人。这样一来,我的担子一下子轻松了不少。

于是,按照计划,我和王瑜导读第一个论题,王宏健和潘钰盟导读第二个论题,闵志伟和赵瑜导读第三个论题,朱懿明和余海波导读第三个论题。
《现象学之基本问题》是海德格尔1927年的讲稿,同时它也可以看成是《存在与时间》的续篇。它原本属于《存在与时间》整个写作计划的一部分,《存在与时间》写到第一卷的第二部分就结束了,而《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便是未完成的第一卷的第三部分。
列维纳斯曾评价说:“在整个20世纪,如果谁想从事哲学,却不到海德格尔哲学中走一趟,那将一事无成。”同时他也格外指出了海德格尔思想的“另一个本质贡献:读哲学史的新方法”。(见《回答——海德格尔说话了》134页)这部《现象学之基本问题》正是体验海德格尔本人哲学和海德格尔阅读哲学史的工夫的一个绝佳机会。
已故学友江绪林阅读此书后曾写道:“凡海德格尔涉足之处,便给人一种其道大光的冲击感。”我亦有同感。书中所涉之哲学史论争纷繁复杂,然而海德格尔笔锋所到之处,天光骤开,仿佛拨云见日,也仿佛红海水分。更为难得的是,海德格尔从未故作惊人语,只是因其准确和平易而使人惊艳。
这里权举几个在我眼里当属“治大国若烹小鲜”的例子:
谈到“谓词”时海德格尔不忘为读者浅析其含义:“谓词的意思是在一陈述(判断)中的被陈述者。”(GA 24, 44. 页码依照德文本,也即中文本边注码,下同)若我们读过逻辑学中对谓词的定义——比如,“谓词是一种关系”,“谓词用以描述个体的属性和个体间关系的部分”,等等——就会知道,海德格尔在定义谓词时已经运用了现象学的基本方法:陈述和被陈述者、判断和被判断者之区分。
当提到范畴时,海德格尔说,“范畴不是形式之类的东西,凭借这种形式人们可以揉捏任何预先给予的材料。范畴是在对合一的着眼中作为统一性的理念出现的东西,是联结之统一性之可能的形式。”(48)若我们细思康德对于“范畴”的特别定义,便知这里的概述是综合了康德“先天综合判断”,“我思之统觉”、“先验知性范畴”之诸种要素后的准确概述。
又比如关于实存(existentia)和本质(essentia)相区分的问题,海德格尔列举了思想史的线索后,给出了一个理解上的指针:“必须在区别无限存在者和有限存在者这两个概念的哲学语境里领会这一问题。”(113)事后我们会发现,这一指针贯彻在海德格尔本章的写作思路和结论中。
在谈论主体性问题时,我也曾惊喜发现,海德格尔把我头脑中模模糊糊的一个印象准确地说了出来:“主体性、自我性意义上的主体-概念,在存在论上是以最内在的方式和subjectum[主词]、hypokeimenon[主词、基底、基质]这个形式的、断言的范畴联系着的,而在subjectum、hypokeimenon之中完全没有包含什么具有自我性的东西。恰恰相反,hypokeimenon乃是现成者、可用者。虽然笛卡尔、特别是莱布尼茨也已预先提及了,由于康德首次阐明了自我是真正的subjectum,用希腊语说就是真正的实体(Substanz): hypokeimenon,黑格尔才能够说:真正的实体就是主体,或者真正意义的实体性就是主体性。”(178-179)这一整段简直就是古希腊哲学和近代观念论最核心的隐秘关联脉络。
在谈论系词相关的逻辑学时,海德格尔居然轻轻松松作出如下断言:“逻辑学有这样一个古老的信念:概念是从判断中发展出来的,并且是被判断所规定的。”(265)这断言其实正是海德格尔说“命题真理的‘场所’在判断中”的依据,而这个知识点恰恰又是逻辑学本身不传授的——它不传授不是因为故意隐瞒而不想说,而是因为过于明显而不必说。
以上只不过是海德格尔解读哲学史之工夫中的“小节”,其真正的大师功力应当体现在整部讲稿的谋篇布局、对主题的条分缕析中。在谈论此书正文之前,我想先说说我们手头的译本以及我们此次阅读的方式方法。
丁耘先生的译本已经三版(2008, 2018, 2022)啦。此译文雅驯可靠,为我们的流畅阅读和准确理解增添不少助力。尤其是丁耘先生为书中出现的古希腊语、拉丁语术语和词句都添加了细致精准的翻译,扫清了语言“拦路虎”,对于哪怕谙熟德语的读者来说,也省却了查找的麻烦。这也正是“后记”中所言“不乏为读者着想处”的译者良心的体现。
我们的读书会分为上午、下午两场,各三个小时。按照分工规划,先由领读人导读,然后便是自由讨论时间。原本只是“读书会”,从这个规划来看,则不免把读书会变成了“讨论班”。事实上,每位参与报告的同仁都完成得非常精彩。
德语所谓“Referat”(报告)可以追溯到拉丁语referre,意思是“关联”,语言哲学中的“指称”(reference)同源于此。Referat的核心含义是“指向一个主题”,它可以被理解为“尽可能地(就这个主题)多说说”(so viel wie es möge berichten)。从具体的操作来看,这种报告也可以被理解为阅读后的“读书报告”,其主要工作是概括大意和梳理思想脉络。
上过“讨论班”的人总是有这样的经验:一门课上完,印象最深的就是自己做报告的那一节课。这是讨论班实行起来的优点,也是必然的缺憾。读书是窃天光,偷得一丝是一丝,因而哪怕一孔之见也弥足珍贵。报告人往往是对文本准备最充足,因而也是问题最多的那个。在一般的讨论班上,大多数时候总是报告人跟教授讨论到课程结束。
由于我们的“读书会”不小心变成了“讨论班”。所以自由讨论的大部分环节,都成了王宏健和我在各抒己见。但提问和回答本身也是不分轻重的。重要的提问比回答更让人印象深刻。我们在哲学里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共识:哲学乃是提出问题,而不是给出答案。我在回答中也经常在思考问题本身,思考如何重新提出问题,或者说,意识到这里居然有此问题。
这便要提到讨论或者说交流的益处和必要性。虽然说我们读书便是与古人交流,但这种交流有一种时间纵向上的单向度,并且会因为“注意力”的缘故而失却横向的联结。同行的问题既把它者的注意力带入视线,同时也提供了对自身缺憾的自省视角。
对于全书的内容,首先需要看到,这部讲稿是海德格尔所有讲稿中最注重“谋篇布局”的一部。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讲存在的四个论题,第二部分讲时间。时间或时间性其实是海德格尔理解存在问题的总的线索(或如《存在与时间》所言,以时间为视域)。存在的四个论题便是“存在问题”的哲学简史。每个论题都分为三个小节,大致都有70页左右。而这三个小节都遵循固定的体例:第一个小节以哲学史写作方式回顾和概述前人观点,第二个小节从现象学角度分析前人观点的得失,第三个小节过渡到海德格尔本人的哲学术语及其思想的阐释。此书写得如此工整,已经不像是讲稿了。它因而也是海德格尔最重视的一部讲稿性著作。在海德格尔厘定自己的全集出版目录后,第一部被编辑出版的全集作品就是此书。此书出版于1975年,当时海德格尔还在世。因而此书也还可以算是海德格尔生前发表作品之一。
存在的四个论题,分别是康德所讲的“存在不是实在的谓词”,古代和中世纪的实存和本质的区别,在精神存在和自然存在之区分中的主体性问题,以及在判断理论中作为系词的存在(以及真理)问题。
为什么是这四个论题?这四个论题是不是可以被理解为存在的四个含义?
其实不是。四个论题是存在的意义在思想史上的几个表现,并不对应于诸如亚里士多德那里“存在的四种言说方式”,或者海德格尔本人对于存在之意义的界说。
很明显,在康德的论题——“存在不是实在的谓词”——中我们看到的是,康德那里的存在,除了系词之含义外,还有“实存”(也即Dasein, Wirklichkeit, Vorhandensein)的含义。康德所谓“存在不是实在的谓词”,说的就是,存在乃是实存,而非本质。就此而言,第二个论题中关于本质和实存的区分已经在第一个论题中被引出了。同时第一个论题也预先提示了“实存”和“系词之是”之间的区别,后者要到第四个论题中加以展开。而第四个论题所谈论的作为系词的存在,它关涉到陈述中的谓述,谓述其实就是事物的本质内涵,因而它实际上关联于“本质-实存”之区分中的本质。
这样看来,第一、二、四个论题之所涉,皆关乎本质和实存的区分。只剩下第三个论题,它处理的是res extensa(广延物)和res cogitans(能思物)之区分下的近代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这一问题乍看之下,无法归入本质和实存的任何一列之下。但细看起来,由于主体性在近代哲学中主要被规定为“自我意识”,所以这一部分是距离作为海德格尔式此在的“生存”的存在最近的阐释。这里的“生存”(Existenz)从词源上来自于“实存”(existentia)。但正如海德格尔强调的,它不同于实存。
在此种关联脉络中,我们似乎已经可以侦知,海德格尔在四个论题中处理的乃是一个自成系统的“存在之意义”问题。这四个论题可以整合到一种有待阐明的存在之意义中。对于这个整合的存在意义的初步阐明,恰恰可以在《存在与时间》第9节处找到:
这种存在者的“本质”在于它去存在(Zu-sein)。这种存在者假若竟谈得上是什么的话,那么这种“是什么”(essentia)也必须从它的实存(existentia)来理解。而存在论的任务恰恰是要指出:如果我们挑选生存(Existenz)这个用语来称呼这种存在者的存在,那么这个名称却没有而且不能有流传下来的existentia这个古语的存在论含义,因为,按照流传下来的含义,existentia在存在论上差不多等于说现成存在(Vorhandensein)。现成存在是一种存在方式,但本质上却是和有此在性质的存在者不相干的一种存在方式。为避免混乱起见,我们将始终把现成状态这个解释性的字眼用来指existentia这个名称,而把生存专用在此在身上,用来指存在这种规定。(《存在与时间》,42)
这段话可以看成是《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之第一部分的概述,反过来,《现象学之基本问题》可以看做是对这一段话所作的长篇注脚。
这段话包含三个意思:
1. 古代存在论中,存在具有本质和实存的区分;
2. 应该从存在者的生存(Existenz)去理解本质。(这里可以近似地误读为“实存先于本质”);
3. (之所以“实存先于本质”乃是误读,是因为)这里的生存并非实存(existentia),实存在当下流行的语境中可以被现象学地概括为“现成在手的存在”(Vorhandensein)。而我们知道,早在胡塞尔意识现象学中,现成在手存在就被视为需要被还原的“命题之物”,海德格尔继承了这一思想,将现成在手存在等同于非本真的理论之物。
因而海德格尔的工作总是分为两步:首先是从传统存在论和认识论视野中拯救出“实存”(existentia, Vorhandensein)这一总是被忽视的含义来,然后再将实存之含义转渡到作为生命/生活之此在的生存(Existenz)上去。
实存之含义在传统西方哲学中总是被忽略,乃是因为在柏拉图主义影响下对普遍物、理念、形式之把握总是始终占据上风。“本质”(essentia)这个概念最直接可以上溯到亚里士多德实体之含义中的to ti en einai(Washeit, Wesen, 何所是)。亚里士多德尽管已经有了对实存的理解,但在古希腊哲学中,实存概念是付诸阙如的。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实存概念出现于对亚里士多德的注释、阿拉伯哲学家阿维森那以及中世纪的托马斯主义、司各脱主义和苏亚雷斯的著作中。
作为现成存在的实存之所以需要被拯救出来,那是因为非如此不足以澄清存在问题之全貌。现成存在的实存涉及我们通常所谓的“外部世界的存在”。一个东西的“存在”,既有它的“什么-存在”,也有它的“如何-存在”。所谓“什么-存在”,就是这个东西的“本质”,它的“实事内涵”;所谓“如何-存在”,就是这个东西的“实存”,它到底在不在这个世上,它是虚构的,还是实际的,是当下的,还是过去或未来的,是潜在的,还是实现的?如此看来,当涉及“实存”时,就会谈论到“模态”。然而,倘若把实存理解为模态中的诸种方式之一——现实性、可能性、必然性、不可能性——则又只是对实存的一种缩减式理解。模态作为逻辑学术语,乃是事物在我们认识中的一种状态,已然不是“实存本身”。
因而,海德格尔从康德论题出发,并非任意。康德把实存理解为“绝对肯定”(absolute Position),是加到陈述上去的“另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并非事物的实在规定之内的实事联系和实在联系,而是整个事物与我关于物的思想的关涉。”(61)康德的这句话的意思在海德格尔看来是,实存不是加到陈述的内容中去的关系,而是加到“我关于物的思想”上去的关系。
如果是加到陈述的内容中去的,那么这个陈述的内容本身就会多出些来。但事实上,在“天是蓝的”这个表述中,当实存加诸蓝色这个谓述变成“蓝色之存在”(Blau-Sein)后,“蓝色之存在”并没有给蓝色这个实事内容增加任何东西。但“蓝色是存在的”确实又增加了点东西,这种增加对康德来说是加在“我关于物的思想”上去的,也就是说,实存是事物与我之思绪的关系。这跟康德对模态的理解若合符节。海德格尔指出,对康德来说,“模态说的是认知主体对在判断中所判断东西的态度。”(48)可能性、现实性、必然性乃是主体对于所判断东西的“态度”。因而,康德能够说:“知觉……是现实性之惟一特性。”(“纯批”,B273;又见 GA24, 63)
这里的困难在于,康德的“知觉”到底何指,以至于能够跟作为“绝对肯定”的实存等同起来?
海德格尔根据现象学的要义,将知觉首先区分为行知觉(Wahrnehmen)和被知觉者(Wahrgenommenes),然后在这两者之外又提出,实存毋宁等于“被知觉者的‘被知觉存在’(Wahrgenommensein)”(65)。也就是说,康德那里的知觉指的是“在行知觉中的被知觉性、被发现性”(65)。到此为止,海德格尔指出,康德对于实存的探索其实仍然欠缺清晰性。“实存就是被知觉性”的缺陷在于,“现成者自有其现成性,实存者自有其实存,即使它不被发现”(66)。
康德以“存在不是实在的谓词”而揭开“实存”的面纱。此一论题最重要的贡献就是表明康德哲学中实存概念的地位。而对于这一论题的准确理解,还取决于对“实在”一词的概念爬梳。如果我们把这一论题中的“实在”误以为当今流行的含义,也即误以为与现实性、实存同义的话,这一论题就变得不可理解。遗憾的是,这一误解在康德专家那里也大行其道。在一些望文生义的写作中,人们普遍把“存在不是实在的谓词”误解为康德在说,“存在不等于(现实性、实存意义上的)实在”,因而,存在对康德来说只是个系词-存在。更有甚者,他们会说,在康德那里,不能说“Gott ist”,而只能说“Gott existiert”,因为“ist”“不是实在的谓词”,不能单单作谓词来用。
以上误读皆归因于未能准确理解“实在性”在康德那里的含义。根据海德格尔,康德的“实在性”(Realität)根源于中世纪的理解,它的意思是“实事性”、“实事规定性”(45)。也就是说,所有先天综合判断中的谓语其实都可以算作实在的,也即,从“本质”之存在来说,它们都是实在的。故而海德格尔可以说:“每一谓词归根结底都是一实在的谓词。”(47)
如果不能抓住康德的实在性概念,就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康德会说“一百个现实的塔勒所包含的并不比一百个可能的塔勒多一丁点。”这是因为,从一百塔勒的实事内容——也即其实在性——来说,不管它是现实的一百塔勒,还是思想上可能的一百塔勒,都没有区别。因为实事内容是思维中的本质物,在“一百个现实的塔勒”这一概念中,并没有更多的塔勒被思维,而是完全一样。但是,一百个现实的塔勒确实比一百个可能的塔勒更多了。因为一百个现实的塔勒可以换回等值的面包,一百个可能的塔勒却什么也不能交换。这“多”出来的就是“实存”,也可以被理解为前述“另一种关系”。实存确实又对“一百个塔勒”之实事内涵增加了一些东西。因而康德会说,本质上的实在是“单纯肯定”,而实存意义上的存在则是“绝对肯定”。
康德的论题将实存的概念置于我们眼前。本着海德格尔前述“这种‘是什么’(essentia)也必须从它的实存(existentia)来理解”的宗旨,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明白了本质和实存的区分,也就明白了海德格尔那里的存在者和存在之间的存在论差异呢?换句话说,本质是否就对应海德格尔那里的存在者,实存就对应海德格尔的存在呢?
答案是否定的。这也正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之存在论意图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最关键之处。从海德格尔的视角来看,本质和实存都各自地属于存在者,但它们自身不是一个存在者,相反,它们是构成存在结构的环节。(见GA24, 109)本质要从实存来理解,但并不是从作为现成在手存在的实存来理解,而是从此在的生存(Existenz)来理解。在此在的生存中——鉴于此在在其生存中领会存在——存在的结构(或者说生存论的基本建制)得以打开,或者说,得以“展开”。存在的“展开状态”(Erschlossenheit)使得存在者的“被发现状态”(Entdecktheit)得以可能。存在者的被发现状态和存在的展开状态才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论差异”。(见GA24, 94页以下)
同时,这里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对海德格尔来说,存在的展开状态就是在此在自身中的展开、开启(Erschließen, Aufschließen)。(参见GA 24, 307)从一种生存论的存在论的视角来说,此在的展开状态就是存在的展开状态。这可以从海德格尔前期的进路——从此在的分析学来探索存在的意义——得知这一点。
就上述而言,我们已经得到了两个结论:1. 在本质和实存之区分中的实存还并不是存在者和存在之差异中的存在,也正因如此,现象学需要对现成在手意义上的实存保持警惕:现成在手存在在现象学中从来都是理论态度下的非本真之物;2. 要在此在的生存中揭示存在的意义。这涉及到对此在之生存论特性的分析,同时也关联到近代认识论中的主体性(这恰恰是第三个论题的内容)。
对于中世纪哲学中本质和实存的区分,值得发问的地方首先以及首要的乃在于,何以会有这样的区分?!
海德格尔引导我们注意中世纪哲学对于“无限存在者”和“有限存在者”、“出于自身的存在者”和“出于它者的存在者”、“必然存在者”和“偶然存在者”、“由于本质的存在者”和“由于分有的存在者”、“非受造的存在者”和“受造的存在者”、“纯粹现实性”和“潜在存在者”之间的区分。这几个区分的根源都在于具有造物属性的上帝那里。依据造物主和被造物的原则,上述区分构成了本质和实存之区分的前提。因为对于造物主来说,本质和实存是同属为一的,“上帝的本质便是其实存”。“上帝是按照其本质不可能不存在的存在者。而有限存在者则可以不存在。”(110)因而,本质和实存的区分乃是因为我们把眼光落到有限存在者身上而来的。
那么,有限存在者是基于什么而产生了本质和实存的区分呢?在这里,海德格尔通过对托马斯主义、司各脱主义和苏亚雷斯的分析概括了三种不同的区分原则。对托马斯·阿奎那及其学派来说,这种区分是“实在的区分”(distinctio realis),也就是说,实存被认为是附加到事物之实在内容上去了另一种实在性,托马斯持“双重实在性”说。同时在这里,托马斯与康德的区别在于,托马斯认为,实存是附加到事物上去的另一种实在性,而康德认为,是“对认识能力的关系”,也就是前述“被知觉存在”。而司各脱主义则把本质和实存之间的关系理解为“模态的(形式的)区别”(distinctio modalis[formalis]),也就是说,这种“被创造而存在”(Esse creatum)被理解为modus ejus(它的模态),这就是说,根据司各脱,实存以现实的方式属于现实存在者,但它不是事物。最后,苏亚雷斯则把本质和实存的区别理解为“理性的区别”(distinctio sola rationis),也即,这种区分只是一种概念上的把握,苏亚雷斯认为自己的观点跟司各脱实质上是一致的,他们共同反对托马斯的观点:本质和实存的双重实在性。因为对他来说,托马斯主义的错误在于,本质和实存如果是两个事物,那么它们如何合为一个存在着的统一体呢?
海德格尔在他对苏亚雷斯的阐释中,发现了苏亚雷斯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拓展和发挥。海德格尔说:“苏亚雷斯把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指点——在每一个被思维者中,无论它被思维为现实的还是可能的,存在都被共同思维了——转用到实存上去了。”(136)换句话说,苏亚雷斯认为,实存就是这么一个不对现实的何所是添加任何东西、而只是被共同思维到的东西。他通过论述潜能和实现的关系进一步阐明了实存的这一特性。因为在实现之前,物的本质和潜能是没有本己存在的。而当这一潜能者通过创造转为实现时,“不能将这一转化理解为可能者扬弃了一种存在方式;而应理解为它首先接受了一种存在”。(137)潜能转为现实,便是这一被上帝所思维的潜能在上帝的创造中成为真正现实的东西。这样一来,实存其实可以被理解为潜能的实现。
本质与实存的关系在苏亚雷斯那里成为了潜能及其实现的关系。这一对应关系同样也可以在沃尔夫对于实存(Existenz)的定义中看到。沃尔夫将实存定义为“潜能的补全”。本质在莱布尼茨那里被理解为possibilitas,则是从另一个方面揭示了可能性与本质之间的同一性。从近代开始,人们得以用“现实性”来指代实存意义上的存在,这一点跟本质-实存和潜能-实现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分不开的。
我们发现,现在已经从谈论实存问题而转向了潜能-实现之间的转化。换句话说,实存问题被认为是可以从潜能-实现之间的转化而加以说明。这便是苏亚雷斯的一个关键性的指引。但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这还不够。苏亚雷斯只是解决了本质和实存同属于一个存在者的问题,也即,本质作为潜能,实存作为实现。因而苏亚雷斯避免了托马斯“双重实在性”的困难。但是,问题还在于,潜能和实现的“转化”还倚赖于背后的创造和制作的概念。因而,从潜能-实现的转化来理解本质和实存,实际上包含有上帝的创造和制作的观念。只不过苏亚雷斯和托马斯的区别在于,就像海德格尔指出的,托马斯“纯粹从演绎的方式推进”,将被创造者的实存和本质视为两种实在地有所分别的事物;而苏亚雷斯则试图就现实者自身来处理本质和实存的问题,但他的失误在于,还没有让现实者成为“终审法庭”。(见GA24, 139)
在此基础上,对于本质和实存之区分的基本的指引已经产生,那就是基于创造和制作的潜能-实现之转化。但这里需要郑重指出的是,对海德格尔来说,我们无须首先假定上帝这个“无限存在者”的概念才能理解创造、制作以及实现,而是可以回溯到“某个不确定主体的动手施行(Handeln)上”(143)。实存之“现成在手性”(Vorhandensein)就是该现成者仿佛来到手前(vor die Hand kommt),成为一个“手头之物”(ein Handliches)。但这可以不是“上帝之手”,且首先不是“上帝之手”,而是人类此在之手。
对海德格尔来说,经院哲学所领会的实存可以回溯到“此在的制作性施为”(das herstellende Verhalten des Daseins)。归根结底,“实现”乃是此在制作性施为中潜能的转化。事物的现实性应该从其实现来理解,而实现包含有一种“来到手前”,也就是向着主体、向着此在的关系:这是作为被制作者的现成在手性。
海德格尔说:“我们尝试在这一晦暗中显明某些东西,尝试阐明essentia和existentia概念的本源,尝试表明,这两个概念在多大程度上源于一种存在领悟,而这种存在领悟是从实现的角度,或者像我们一般所说,从此在之制作性施为的角度来统握存在者的。”(147)
指出essentia和existentia起源于此在之手,也即此在的制作性施为之后,还需要进一步看看,这一此在制作的事件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海德格尔认为,在制作中,首先有模型(Vorbild),然后才有构成之形象(Gebilde)或铸成之模印(Geprägte)。外观(Aussehen)就是模型。因而外观是首要的。这个外观不是知觉上得来的外观,而是制作中首先被要求的外观。如果外观只是知觉上得来的外观,那么它其实应该根源于事物本身的“形象”(morphe)或“肌理”(Gepräge)。正因为它是制作中的外观,是“模型”,所以它是先天的,先于具体存在者的。而“外观”正是“理念”。“物的这个被先行获取与先行视看的[外]观,正是希腊人用eidos[理型、相]、idea[理念]在存在论上所意指的东西。”(GA24, 150)eidos是“物先行之所已是”(das, was ein Ding im vorhinein schon war)。而这也正是亚里士多德用to ti en einai(das, was ein Seiendes schon war)所规定者。
如此一来,本质和实存的概念就在制作行为中呼之欲出。本质俱都有赖于、或着眼于制作行为。制作中的塑形(Gestalten)、构形(Bilden)、成器(Erzeugen)就是一种“让-出生”(Herkommenlassen)、“让-源出于”(Herkommenlassen-aus)。本质的规定性可以看成是在塑形中的被塑形者、在铸造中的被铸造者、在构形中的所构之形象、在成器中的所成之器和被完成者。(GA24, 152)同时,制作也包含着实存的概念:“但生-产制作(Herstellen)同时意味着:带入可通达者的或窄或宽的圈子里,过来(her),来到这里(hierher),进入这个‘此’(Da),以至于被制作者就其自身自为而持立(für sich steht),并且作为自为而持立者保持为可现身的现前而有(vorliegt)。”(GA 24, 152)希腊语的hypokeimenon(主词、基地)在海德格尔看来,就是“现前而有者”(Vorliegende)。海德格尔说:“在制作性施为中被领会的存在正是完成者之自在存在。”(GA 24, 160)
在这里,海德格尔的核心观点是,传统形而上学中的本质和实存的区分,都是在制作的行为中得以产生的。这里他当然有意放弃了在古代和中世纪有关制作以及创造的最重要的思想源泉:造物主或者神。如果说古代传统形而上学依赖于制作概念,那么,这种制作也是来自造物主或者神的制作。人类的制作只是对造物主或神的制作的“摹仿”。按照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有关目的论的说法,人类技艺中的目的,也只不过是对自然本身所拥有的目的的摹仿。所以自然的目的论在先,人类技艺的目的论在后。但是,在海德格尔这里,一个超越的神的渊源毋宁也是因为此在本身之超越的“何所向”。此在的制作性施为才是人们源初地体察到目的这回事的源泉。故此,海德格尔可以将古代存在论笼统地概括为乃是以制作行为为基础的一种“被制作的存在”(Hergestelltsein)。
如此一来,问题转向到此在以及此在的行为。此在“何德何能”,得以堪当此存在论源泉的大任?
在第三个论题中,海德格尔处理广延物和能思物,也即自然存在和精神存在的问题。显然,广延物和能思物也是存在的基本方式。然而这不是古代形而上学中本质和实存的区分,而是近代认识论视角下基于主体和客体的区分。广延物是客体的存在,能思物是主体的存在。这里涉及的根本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经典的认识论问题:内在的主体如何实现外在的超越?
对海德格尔来说,主客体问题的解决首先依赖于这个问题的正确提出。海德格尔多次提到,在主客体关系问题的提法中,如果首先把主体设为内在的, 把客体设为外在的,然后再求问它们之间的超越性联结,那么这个问题就永远得不到解答。因为问题自身是“颠倒的”。(见GA24, 306)一种正确发问的关键在于对主体性进行更彻底的发问。
海德格尔注意到,近代认识论总是从主体出发来认识对象,但认识论里的主体并不是从存在论上来理解的。而海德格尔的任务则是要从对近代认识论的主体的考察,切入到关于此在之存在方式的基础存在论中。
海德格尔选择康德为考察对象,来研究近代认识论中的主体的主体性。康德的先验认识论是最接近胡塞尔意识现象学的。事实上,我们在康德对自我的划分中,也可以看到胡塞尔现象学中诸种自我的分类。
按照海德格尔,康德的自我分为:先验的位格,心理学的位格和道德的位格。“先验的位格”就是先验认识论的主体,它是承载着一切知觉活动的那个“总是伴随我的一切表象”的“我思”(179),它是“统觉自我”(180),是“一切行表象、一切行知觉的根据”(181)。从这个方面讲,先验的位格相当于胡塞尔的“先验自我”,“原-我”。“心理学的位格”就是通过内感觉而得到的经验的自我,也即自我-客体。这就相当于胡塞尔那里的“经验自我”。而“道德位格”是在道德感受中的“自我彰显”,它涉及主体的道德行动。海德格尔指出,道德的自我意识不是“感性-经验”的,也不是“作为思维主体之自我的理论知识和思维,而是使自我彰显在其非感性的规定性(即其作为行动者的自身)中”(188)。这里涉及的是行动者自身的行为。这一自我的层级类似于胡塞尔在“观念II”中谈论的“位格之我”,胡塞尔借此而谈论使得意识之河流得以可能的“源初能力”(Urvermögen)。可见这一自我层级是现象学所洞察的自我之最深层的规定。海德格尔从康德的“敬”(Achtung)诠释出了道德感受的现象学意味。海德格尔认为,对道德法则的“敬”并非一个单方面的“屈从”,它同时也包含着自身的彰显。“必须看到,在作为感受的敬中向来包含着‘听命于’意义上的‘对法则有感受’。这个‘听命于’按照其内涵(我所听命的东西,我对之有‘敬’之感受的东西)同时就是(作为在最本己尊严中的自我彰显的)自我提升。”(GA24, 192)对海德格尔来说,这便是“敬之意向结构”。由此海德格尔也反驳了舍勒对康德道德哲学的“形式主义”批评。
“道德位格”乃是以“敬”之方式拥有自身。“敬”其实是“对自己自身的‘应责式存在’(Verantwortlichkeit)”(200)。对康德哲学的现象学分析让我们看到了康德“自由意志”中所包含的那个实际生存着的此在的基本建制。海德格尔举康德的一句话——“理智乃是这样一种东西,其概念正是作为”——解释道:“精神性的存在者正是这种以作为之方式存在的东西。”(200)在这里,我们也发现了,为什么海德格尔认为,我们对一个制作施为着的此在的分析,或者说,对于此在之生存的分析,就是最接近于找到“实存”的工作。因为:“行动是一种现成存在意义上的‘实存’。”(200)
但是要格外注意的,道德位格和先验位格并未统一起来。我们在道德位格那里看到了以“敬”的方式对自由此在(自由意愿)的存在论规定。按照通行的康德解释,在道德哲学中,康德的“物自身”以实践方式发挥作用。但是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的“物自身”是不可知的。换句话说,道德位格在其实存中显现自身(“自由是道德的存在理由;道德是自由的认识理由);纯粹的先验自我的“实存”是不可知的。为什么纯粹自我的实存“不可知”呢?因为对康德来说,首先作为“我思”的自我是纯粹的自发性,若要对“我思之我”做出规定,则需要某种东西被给予我。但被给予性依赖于接受性,依赖于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直观。而我若通过将范畴联结到直观的方式来表现自我,就已经把“我思之我”视为自然物,是把纯粹自我案子调换为现成者的自我。所以海德格尔这样为康德总结道:“纯粹自我自身决不会作为为了规定(也即为了范畴之应用)的可被规定者被给予我。因而,对自我的存在者层次上的认识便是不可能的;由此导致,对自我的存在论规定便也是不可能的。”(GA 24, 205)
那么,“对自我存在者层次上的认识”(eine ontische Erkenntnis des Ich)真的不可能,由此对自我的存在论规定(eine ontologische Bestimmung des Ich)也不可能了么?当然不是。海德格尔在“康德书”(GA 3)中试图将康德的先验哲学理解为一种“形而上学”,便是这种努力的一番尝试。而在GA 24中,我们从海德格尔对康德的屡次三番的引入中,也发现了这一动机。这一分析的目标在于,通过对主体性的彻底阐释,转变到以此在的生存论建制分析的存在论进路上来。
现在的问题是,海德格尔如何向我们表明,对于此在的“生存”的分析,是一种涉及到此在自身之“实存”以及事物之“实存”(这个实存是存在者层次上的)的一种生存论的存在论?换句话说,“生存”(Existenz)如何彰显“实存”(existentia)?
对此,《存在与时间》其实早有关键性的提示:“我们总已经活动在对存在的某种领会中了。”(SuZ, 5)“对存在的领会本身就是此在的存在规定。”(SuZ, 12)“此在在生存中领会存在”,这件事如此普通和平常,却又怎么成为构筑一种崭新的存在论的关键?
这里首先涉及此在达及存在的方式:自己的生存。换句话说,此在本身已经是一个在客体之世界中实存的存在者。这一点跟认识论完全不同。认识论把主体视为与对象(自然存在,res extensa)分离的精神存在(res cogitans),因而先行把主体和客体隔离地对置起来。但海德格尔认识到,生存本身就是此在的存在方式。“对于此在而言,随着此在之生存已经以某种方式揭示了一个存在者以及与存在者的一种关联,这一点是无需专门客体化的。”(GA24, 224)此在在生存中与客体打交道,此在已经绽出地生存(ek-sistiert)在客体中。“生存意味着:自行施为着在存在者那里存在。”(sich verhaltendes Sein bei Seiendem)(GA24, 224)
其次,此在在生存中自行指向存在者,同时,在这种自行指向中自身成为“随同被揭示之存在”(Mitenthülltsein)。这是此在生存中的意向性的两个方面。此在的意向性不仅通过“操心”(Sorge)指向世内存在者,同时也“反身”指向自身。同时,这一反身指向并不是另一个意向性的指向,而是在每一个指向存在者的那个意向性里同时进行的对于自身的指向。海德格尔说:“属于意向性的不仅有‘朝着某某-自行指向’,不仅有它所指向的存在者之存在领悟,而且还有(自行施为而与某物相关的)自身之‘随同被揭示存在’。”(GA24, 225)简单而言就是,我们在领会世界的时候,同时也领会我们自己。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在领会世界的同时领会了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总是包含着世界的我们,我们对于世界的探索有多深多广,意味着我们的自我有多深多广。
这一点是符合胡塞尔现象学的基本原理的。对胡塞尔来说,事物在意向性中的构成同时就是先验自我的自行构成。但是,海德格尔也有批评胡塞尔的地方。对胡塞尔来说,对意向性结构及其构成的揭示依赖于现象学的“反思”,而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意向性的反身结构,那个自身的“随同被揭示存在”并不能通过反思而得以揭示,而是通过诠释学。
诠释学就是此在分析学,就是早期弗莱堡时期所谓的生活实际的诠释学。诠释学解释什么?解释生活的处境,也就是胡塞尔现象学中的“视域”。生活的处境概念比意识之当下的“视域”概念更具有时间性、历史性的沉淀和展望要素。处境——或者像阿伦特所言“人的境况”——是一种先于诸存在者的显现而预先就有的对世界的领悟。总体来说,它被海德格尔概括为“在-世界-之中-存在”。这个短语既揭示人类此在之生存的现实性,也揭示此在生存中与世界相关联的先天的可能性。此在现实地生存于世,同时此在作为“能在”而领会着地生存于世。这是世界中的某物与我们形成并非只是观念性的、心理性的关联,而是实实在在的实事性的切身联结的原理所在。正因为人的生存是“在-世界-之中-存在”,此在已经先行于意识主体的“发现”而与世界发生了联系。世界联系以存在领悟的方式包含在此在的存在方式中。意识到某物,或者说“存在者的被发现状态”,是此在之存在方式中的一种。
海德格尔以此方式澄清了我们的生存和形而上学的本质与实存的关系,以及我们的生存和对世界的认识之间的关系。但是,且稍等,从近代认识论以来,存在都是在认识或者说感知中被发现的。存在的命题是以真理的样式而产生的。那么,存在与真理的关系如何?这就要进入到第四个论题——作为系词的存在——中去了。
系词之存在,从汉语来说,这里的存在应该用“是”来表示。因为汉语中是用“是”来担任主语和谓语之间的联结词,而不是用“存在”。所以,这里讨论的是系词之是和存在之间的关系。
什么是“系词之是”?康德说:“某种东西可以是仅以关系方式被设定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仅被思维为对作为一物之标志的某种东西的关系(respectus logicus, 逻辑关系);然则是,亦即对该关系的肯定,无非就是一个判断中的联结概念。”(《证据》,77,见GA 24, 255)简言之,系词联系主词和谓词,所以称为“系词”(copula)。
为什么在主词和谓词之间需要有一个“系词”呢?海德格尔通过检查亚里士多德对“系词之是”的理解,指出:“这个‘是’所意味的东西,并非一个厕身于诸物之列的存在者,一个如同诸物那样的现成者,而是en dianoia,存在于思维之中。这个‘是’乃是综合,确切地说,乃是亚里士多德所谓synthesis noematon [所思者的联系],在思维中的所思者之被联系性。”(GA 24, 258)也就是说,系词之是所表达的就是所思之物的联系性,且它“存在于思维之中”。
接着,海德格尔还分别考察了霍布斯、穆勒、洛采对系词之是的理解。这三个人的理解带有递进层次。首先,霍布斯从单纯的实在内容的意义上来理解系词之是。从他的“极端唯名论”立场来看,主词属于实存,而谓词属于由系词所关联的真理内容。对霍布斯来说,“如果没有系词‘是’,表达何所是与quidditas(何所性)的抽象名称便不可能存在。按照霍布斯,抽象名称源于系词。”(GA24, 266) 对他来说,系词之是“在被说出的思维中,在命题中”。
而穆勒则意识到,命题中的“是”既表达实在内容,也表达实存之存在。穆勒说:“在‘苏格拉底是正义的’这个命题中,可以看到,其蕴涵的不仅是:‘正义的’这个质能够被肯定地加到苏格拉底上;而且还有:苏格拉底存在(ist),也就是说,实存(existiert)。”(穆勒《逻辑体系》,86,见海德格尔GA 24, 275) 穆勒从这一分析中看到了“是”的歧义性,或者说,系词之是具有双重含义。海德格尔指出:“他相信在系词‘是’(ist)中有着一种双重含义:它一方面意指联结功能或者说符号功能,但同时同样意指实存。”(GA 24, 276)有鉴于此,穆勒通过“本质的命题”和“偶然的命题”来理解其中分别(GA 24, 277),同时也借助于在命题陈述中采用“意指”和“是”来分析不同的指代。(GA24, 279-280)总体而言,穆勒强调了系词之是中的“实存”之含义。
洛采同样指出了系词之是的“联结”意义,和它表达“真性存在”(Wahrsein)的功能。只是洛采得出这一结论的方式值得一提。他认为,并没有“否定性系词”一说,所谓“S不是P”指的是对于“是P”这一思想的否定,而不是否定S和P之间的联结。他因此而发现系词之是的“双重判断说”。也就是说,S之“是P”表达了命题内涵的主要思想,同时还有一个“是的,就是这样的”、“是的这是真的”的附加思想。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实事内容的判断中,都包含着对这一实事内容本身的再判断,后者相当于对这一实事内容的“真性”的判断,代表了我所认识到的实事内容与对象的“对象性”合一。所以,在系词之是的联结,也即在判断中,也总有一个存在被表达了,这里的存在可以表示为“真的被判断存在”或“是被判断为真”(wahres Geurteiltsein)。(见GA 24, 285)
当然,海德格尔也眼光犀利地看到了其中的缺陷。上述可以说“从系词之是推出存在”的路径,恰好是新康德主义的奠基性观点。在他们那里,“认识等同于判断,真理等同于被判断存在,等同于对象性,等同于有效意义”。(GA24, 286)我们应该可以看到,这里包含着一种观念论意义上对于实存的缩减,这也正是观念论被实在论所批评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真理的两种含义:一种是通过系词的联结所揭示的实事内容,另一种是它的对象性的存在。这是表达在系词之是中的两种含义。系词之是既可以表达本质意义上的存在,也可以表达实存意义上的存在。海德格尔说:“由于一切存在者都被‘什么存在’(Wassein)和‘如何存在’(Wiesein)所规定,并且作为存在者都在其何所是与如何是中得到揭示,所以系词就必然是多义的。然而这种多义性并非什么‘缺陷’,而只是表达了存在者之存在的自在多重结构,因而也就表达了根本上的存在领会的自在多重结构。”(GA24, 291)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真理与存在在认识论和存在论上向来就有的一致性。
但是,海德格尔并不是从“系词之是”来揭示真理与存在的相互共属。对海德格尔来说,真理发生的“场所”并非在“判断”,这一点可以参考《逻辑:对真理的追问》(GA21)。对海德格尔来说,从陈述的命题出发来理解主词和谓词之间的联结关系、由此来理解存在之本质和实存是不充分的。对系词的追问中,需要被问的是“什么样的纽带造成了该关联之统一性?”(GA24, 292)逻辑学只能描述性地分类阐明词、含义、思维、所思、存在者之间的关系,但很明显,逻辑学不能阐明这些关系之所由来。
对此,海德格尔单刀直入地指出,“系词之是”之所以能够表达出存在的多重含义,乃是因为说出“系词之是”的是此在自身。我们很容易看到,在“命题”的陈述中,真正的“陈述者”是此在自身。正是因为有此在自身作为陈述者,在命题之陈述中的主谓联结才得以可能。海德格尔说:
由于“在-世界-之中-存在”在本质上属于此在,而此在自身之被揭示也与之相一致,所以每一个实际生存着的此在——这意味着言说着的且说出自己的此在——已经领会了在它的存在中的不同存在者之多样性。系词的漠然无殊并不是什么缺陷,它只是描述刻画了所有陈述的次级特征。命题中的“是”之所以能够达到其含义上的不确定性,这是因为“是”作为被说出的东西发源于说出自己的此在,这此在已经如此这般地领会了在“是”中被意指的存在。“是”在命题中被说出之前,它已经从实际的领会中得到其差异区分。(GA24, 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