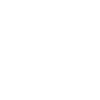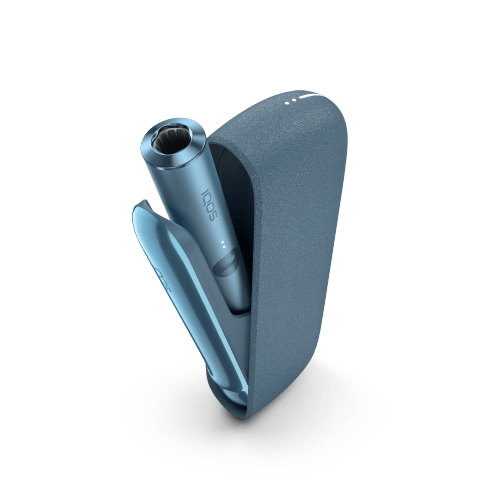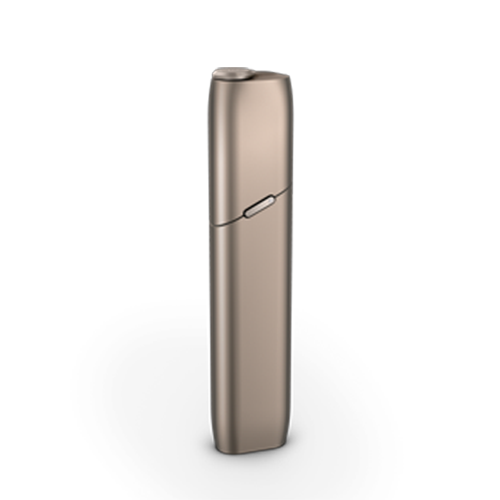重新审视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会通

尽管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在思想背景和文字表述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这并不排除他们之间有某些会通的可能性:一、马克思的此岸真理论和海德格尔的实存哲学,都是对柏拉图主义的颠倒;二、他们都将实践作为人的基本规定,都有改变现实的思想追求;三、他们把共在作为人的另一项基本规定,致力于探索如何通达本真的共在。
一、基本形象的会通
马克思和海德格尔都是来自德国的大师,都是欧洲哲学史上举足轻重的思想家。有关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比较研究早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尽管他们的思想背景有巨大差异,但是,这并不排除有一种会通的可能性。重新审视海德格尔和马克思的会通,自然离不开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直接评价:“纵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我们将要说明的是,对形而上学的颠倒,乃是他们两位在基本形象上可以会通的表现。
那么,何谓柏拉图主义?依照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叙述,柏拉图划分了两个世界:一、可以感觉的、流动变化的世界;二、可以思想的、恒常不变的世界。后者是理念的世界,理念是永恒的,不发生变化,其它事物通过分有理念而获得其存在。海德格尔在阐释尼采时,多次提到“柏拉图主义”,亦即有关“两个世界”的学说:“这个尘世的、变化的、可为感官所达到的世界之上,有一个超感性的、不变的彼岸世界。后者是持续地持存着的、‘存在着的’、因而真实的世界;前者是虚假的世界”。因此,“柏拉图主义”意味着感性世界和超感性世界的区分和排序。
“柏拉图主义”不仅意味着感性世界和和超感性世界的区分和排序,而且具有实质性或质料性的内涵。在柏拉图看来,有两类事物:一类事物是可以变化和可以生灭的,诸如食物;另一类事物牵涉着永恒的东西,诸如知识、理性、美德。这两类事物比较而言,后一种更加真实,因此,总的来说,“保证身体需要的那一类事物是不如保证心灵需要的那一类事物真实和实在的”。这就引出了柏拉图有关灵魂的划分和秩序,在他看来,人的肉体欲望和激情都要服从理智的引导。因此,柏拉图主义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抬高精神追求而贬低肉体享受。
海德格尔指出:“随着柏拉图把存在解释为idea[相],形而上学(Meta-physik)就开始了......而且,因为形而上学始于对作为idea[相]的存在的解释,而这种解释一直是决定性的,所以,自柏拉图以降的一切哲学都是‘唯心主义’(Idealismus)——这是在一种清晰的意义上来讲的,意即:人们是在理念中、在观念性的和理想性的东西中寻找存在。因此,从形而上学的奠基者角度出发,我们也可以说:一切西方哲学都是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柏拉图主义本质上意指着同一个东西”。因此,从观念出发解释现实世界,不仅是德国唯心主义的表现,追根溯源,乃是柏拉图主义的表现。
首先,如何理解马克思对柏拉图主义的颠倒?马克思对柏拉图主义的颠倒,表现为他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他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曾经得益于费尔巴哈的启发。费尔巴哈已经认识到了黑格尔哲学的弊病:黑格尔将绝对观念置于优先地位,其实是在信仰世界之外的造物主;黑格尔是“从绝对的和不变的抽象出发,就是说,说得更通俗些,他从宗教和神学出发”。因而,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也表现为对宗教的批判。他曾指出,宗教是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颠倒的世界”、“人民的虚幻的幸福”、“人民的鸦片”。在费尔巴哈的启发下,马克思提出“废除作为人民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宗教即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唯心主义讲究的乃是“彼岸的真理”(das Jenseits der Wahrheit),而马克思则致力于建立“此岸世界的真理(die Wahrheit des Diesseits)”。可以说,马克思致力于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黑格尔哲学乃是彼岸的真理,而马克思哲学乃是此岸的真理。
关于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还有更详细的表述:“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vom Himmel auf die Erde);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von der Erde zum Himmel)”;不是从设想、想象和思考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leibhaftige Menschen)”,真正的出发点乃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wirkliche tätige Menschen)”;“不是意识(Bewusstsein)决定生活(Leben),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不是从观念(Idee)出发解释实践(Praxis),而是从物质实践(materielle Praxis)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die Ideen formationen)”。通常人们将马克思这番论述称作唯物论即唯物史观,这当然是无可置疑的。不过,从世界哲学的历史演变来看,马克思的这番论述意味着对观念论的颠倒、对彼岸真理的颠倒、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对柏拉图主义的颠倒。

马克思不仅颠倒了彼岸的真理,而且建立了此岸的真理。换言之,他在颠倒旧价值的同时,也在进行新的价值设定。进行新的价值设定,就意味着虚无主义。因此,海德格尔说:“马克思达到了虚无主义的极致。”这并不是在责备马克思,而是在表达对马克思的赞赏。因为“虚无主义”这个概念,在尼采和海德格尔那里有两种用法:依据其第一种用法,柏拉图主义是虚无主义,因为“对于如其所是地存在的世界,他断定它不应当存在;对于如其应当是地存在的世界,他断定它并不实存”;依据其第二种用法,尼采所讲的“对以往一切价值的重估”,是虚无主义。这是一种积极的虚无主义,既然以往价值不再发挥作用了,那么,就要建立新的价值或新的价值秩序。
其次,如何理解海德格尔对柏拉图主义的颠倒?早在20年代阐释亚里士多德之际,海德格尔就开始了对柏拉图主义的批判:哲学的道路乃是从具体事物通往普遍事物,不可像柏拉图那样把具体事物视为“不存在者”(me on),试图通达什么更高的存在。这样做,乃是把真正的存在者视为不存在者。同时,海德格尔认为,柏拉图的这种失误,亚里士多德看得一清二楚。后来,他在阐释尼采的时候,对柏拉图主义的批判继续保持着:“存在的同一本质,即在场,柏拉图思之为idea[相]中的koinon[共性],亚里士多德把它把握为作为energeia[实现]的tode ti[个体、这个]。由于柏拉图决不能让个别存在者成为真正存在者,而亚里士多德却把个别之物纳入在场来加以把握,所以,亚里士多德就比柏拉图思考得更希腊,也就是更乎合原初确定的存在之本质”。
海德格尔在批判柏拉图主义时,同时也在积极探索,尽可能使用自己的字语去刻画柏拉图主义。首先,他区分过三重意义方向——“内涵意义”(Gehaltssinn)、“关联意义”(Bezugssinn)和“实行意义”(Vollzugssinn),并且将“内涵意义”称作“什么存在”(Was-sein),将“关联意义”和“实行意义”合称作“如何存在”(Wie-sein),同时指出了传统哲学的弊端——片面强调内涵意义,掩盖了实行意义。海德格尔的真正意图在于表明“如何存在”优先于“什么存在”,只是没有明确讲出来。其次,他将传统哲学的弊端重新概括为“什么存在”(Was-sein)优先于“如此存在”(Daβ-sein)。这时候,他的思想意图就更加明显了。
在《存在与时间》中,他明确提出“此在的本质在于其实存”(Das Wesen des Das ins liegt ins einer Existenz),“实存先于本质”(der Vorrang der exist entia vor der essentia)。这里使用了“本质”和“实存”两个基本字语。海德格尔后来的做法是,将“什么-存在”-“如此存在”和“本质”与“实存”这两组字语同时付诸使用。例如,他将亚里士多德《范畴篇》有关两种实体的文字进行了自己的阐释:“第一位意义上的在场乃是hotiestin[如此存在]中被表达出来的存在,即如此-存在(Daβ-sein)、existentia[实存]。第二位意义上的在场则是在tiestin[什么存在]中被追踪的存在,即什么-存在(Was-sein)、essentia[本质]。”“亚里士多德对这个区分的阐述就揭示了后来所谓的existentia[实存]对于essentia[本质]的优先地位。”
在海德格尔看来,形而上学自古以来就把存在区分为“本质”(essentia)和“实存”(existen-tia),用他的字语来说,就是“什么-存在”(Was-sein)和“如此-存在”(Daβ-sein)。这就是他刻画形而上学的新模式。笼统而言,柏拉图主义是本质主义,而海德格尔则是实存哲学或实存主义。这样看来,马克思和海德格尔都是对柏拉图主义的颠倒,都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倒,在这个基本形象上,他们是可以会通的。当然,他们在思想背景和言说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这是不可避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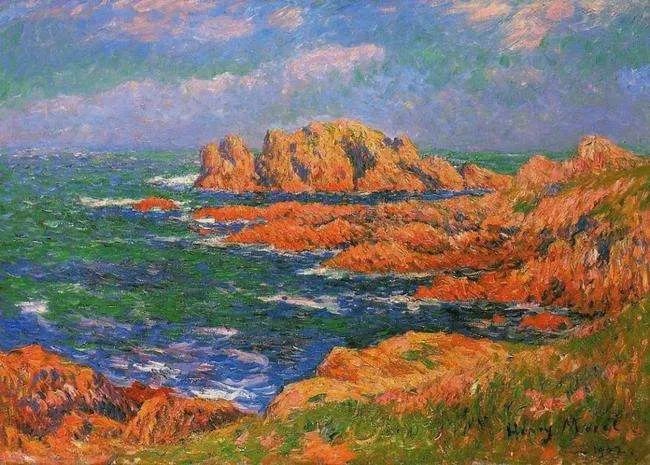
二、实践论的会通依据
海德格尔生前公开出版的作品,他在1927年提出:“日常在世的存在,我们也称之为在世界中与世界内的存在者打交道(Umgang)。这种打交道已经分散在形形色色的诸操劳方式(Weisendes Besorgens)中了。”这种打交道最初是人与用具的打交道,然后通过用具的使用者或消费者延伸到人与人的交往。依据这一点,海德格尔的传记作家萨弗兰斯基曾经比较过海德格尔和马克思:“对马克思来说,人的根是从事工作(劳动)的人,但是在海德格尔那里,人的基本规定是‘与什么打交道’。它是比‘工作’(劳动)宽泛得多的东西。马克思把‘工作’(劳动)定义为‘与自然的材料(物质)交换’。海德格尔的‘打交道’尽管也联系到(物质的、自然的)世界,但是同时也联系着自身世界(自身领会)和共在世界(社会)。”依据萨弗兰斯基的这种评论,可以看到,海德格尔与马克思实际上都把“实践”看作人的基本规定,只不过,海德格尔首先使用的字语是“打交道”(Umgang),马克思首先使用的字语是“劳动”(Arbeit)。
这是海德格尔与马克思在实践论上可以会通的第一个表现。尽管《存在与时间》并没有提及马克思,但是,海德格尔后来多次提到马克思的“劳动”概念。1931年夏季学期,海德格尔明确提到:“人与其所制作的作品具有关联。因而,在《存在与时间》中才谈及与用具的打交道(Umgehen mit dem Zeug);这倒不是为了纠正马克思或者建立一种新的国民经济学,而是来自一种源初的世界领会。”海德格尔的实践论源自他对希腊哲学的阐释,特别是他对亚里士多德“实现”(energeia)的阐释,energeia作为实现活动本身就意味着与作品(ergon)打交道。而马克思的实践论,自然是源自他的政治经济学背景,所以,在马克思那里,“劳动”(Arbeit)首先就是生产活动(Produktion)。1946年,海德格尔再次提到:“人们要摆脱那些关于唯物主义的朴素观念以及那些以唯物主义为目标的廉价反驳。唯物主义并不在于它主张一切都只是质料(Stoff),而倒是在于一种形而上学的规定,按照这种规定,一切存在者都表现为劳动的材料(das Materialder Arbeit)。”1957年,海德格尔更是直接引用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劳动的原文:“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在海德格尔看来,马克思恰好阐明了技术时代的真理:在技术时代、工业时代、经济时代,“生产劳动规定着现实的一切现实性”。
尽管用词、思想背景不同,但却可以说,海德格尔和马克思都将实践看作人的基本规定。这是海德格尔与马克思在实践论上可以会通的第一个表现。第二个表现则是,面对实践交往的现实状况,海德格尔和马克思都深感不满,并且他们都动用了“异化”(Entfremdung)这个字语:1844年,马克思将“异化”上升为一个核心概念,但是这部手稿直到1932年才首次公开出版;1927年,《存在与时间》在刻画日常共在之沉沦现象时起用了“异化”这个字语。至于海德格尔是否借鉴过卢卡奇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不得而知。卢卡奇说:“随着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1927)的问世,它[异化问题]成了哲学争论的中心......在这里,谁起头,谁影响谁的问题并不特别重要。重要的是,人的异化是我们时代的关键问题。”1946年,海德格尔表示:“马克思在某种根本的而且重要的意义上从黑格尔出发当作人的异化(Entfremdung)来认识的东西,与其根源一起又复归为现代人的无家可归状态(Heimatlosigkeit)了。

既然海德格尔和马克思都对现实状况深感不满,那么,改变现实也必定是两位思想家的共同追求。这就牵涉到海德格尔与马克思在实践论上会通的第三个表现,即都有改变现实的思想追求。海德格尔曾在1961年和1969年两次引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哲学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Die Philosophen haben die Welt nur verschieden interpretiert;es kömmt darauf an,sie zu verändern)。海德格尔始终没有反对马克思改变世界的主张,而是特别强调“要想改变世界,就要转变思想”(Allein,die so gedachte Weltveänderung verlangt zuvor,daβsich das Denken wandle),“改变世界要以理论工具作为前提条件”(Und setzt nicht andererseits jede Veränderung der Welteinen theoretischen Vorblick als Weltzeug voraus?),“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其实并不是对立关系”(Gibt es eine nechten Gegensatz von Interpretation und Veränderung der Welt?)。当然,我们知道,海德格尔通常对思想强调的多一些,对行动强调得少很多。但是,这只是字面意思,海德格尔作为思想家特别看重的是思想对于行动的指引意义,既然是指引,那么,这种指引的归宿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行动上。现实生活中,人们缺乏的并不是行动,而是有所指引的行动。
因此,海德格尔并不反对改变世界,实际上,海德格尔是要把实践论的基本结构梳理清楚:改变世界和解释世界并不是对立的,毋宁说,应当结合起来;改变世界当然是需要的,但是,解释世界乃是改变世界的前提条件。马克思德语原文使用的“es kömmt darauf an”,通常译作“问题在于”,这个短语确实是要引出一个关键的东西,但是,还不至于要把前面提到的东西都排除掉;后面的东西更重要,只是就某种角度而言的;倘若换一个角度,前面的东西可能更重要,但是,归根结底,还是要把双方结合起来。1937年,毛泽东的《实践论》很好地处理了这种关系,他一方面转述马克思的话用来强调改造世界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引用列宁的话用来强调理论的重要性——“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967年,卢卡奇在评价列宁时,同样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的互相结合:“就理论家和实践家这两个词最严格的意义而言,他[列宁]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他是一位深刻的实践思想家,一个热情地将理论转变为实践的人,一个总是将注意力集中于理论变为现实、实践变为理论的关节点上的人。”
那么,理论如何引导实践呢?在海德格尔看来,理论(海德格尔式的形式显示的理论)只能给出一些提示(Hinweis),给出一条道路(Weg),具体如何实行(Vollzug),还是悬而不定的,还要保持开放;人们应当在理论的引导下,审时度势,相时而动,开展具体的实行;因为实际生活是变动不居和各个不同的,人们应该把握其具体处境(Situation),而不可执着于一般形势(allgemeineLage)。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亦是如此。1872年,他和恩格斯认为《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当然,“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844年,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原理并不是绝对原理,而是只在一定条件下才发挥作用的原理;毛泽东提到:“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理论对实践的引导,并不是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而是给出大致的方向,实际行动时要参考具体情况,这是海德格尔与马克思在实践论上会通的第四个表现。
此外,还有第五个表现,牵涉到两位思想家对历史的理解。在海德格尔看来,“历史”(Geschichte)不是“历史学”(Geschichte wissenschaft)意义上的“历史”(Historie),毋宁说,“历史是生存着的此在所特有的在时间中发生的历事(Geschehen)”,而“此在的历事,也可以说,是实践(Handeln)的本真意义”。《德意志意识形态》有关“历史”的用词可以与海德格尔相媲美:“一切人类生存(menschliche Existenz)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Geschichte)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Geschichte machen),必须能够生活......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geschichtlicheTat)就是......而且,这是人们......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任何历史观(geschichtliche Auffassung)的第一件事情......”由此可见,无论是海德格尔,还是马克思,实际上都把“历史”(Geschichite)看作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人类生存”(menschliche Existenz),是“历事”(Geschehen),是“创造历史”(Geschichte machen),总而言之,都是“实践”(Handeln)。

三、共在论的会通
按照通常的理解,海德格尔思想的特色乃是个体论。其一,海德格尔对此在的基本规定——此在总是我的此在,也就是“向来我属”(Jemeinigkeit)。这里的“我”可以替换为“每个个体”,此在总是每个个体的此在,于是,有关此在的基本规定就蕴含着个体论。其二,可以标识海德格尔个体论的另一个字语是“个别化”(Vereinzelung)。他说:“畏把此在个别化并开展出来成为‘solus ipse’[唯我]。但这种生存论的‘唯我主义’(Solipsismus)并不是把一个绝缘的主体放到一种无世界地摆在那里的无关痛痒的空洞之中,这种唯我主义恰恰是在极端的意义上把此在带到它的世界之为世界之前。”“此在个别化了,但却是作为在世的存在个别化的。”海德格尔同时动用了“唯我主义”(Solipsismus),在此语境下,其实也就是个别化,也就是向来我属,就是想突出其个体论的基本原则;而且,如上所说,这种个体论乃是在世的个体论。即使海德格尔提到:“存在有本真状态与非本真状态两种样式,这是由于此在根本上是由向来我属这一点来规定的”,这种提法也并没有将共在等同为非本真。
事实上,海德格尔不仅有个体论,也有共在论,而且,在共在论上,海德格尔与马克思可以会通。海德格尔提到:“此在本质上是共在(Dasein ist wesenhaft Mitsein)”;“此在之独在也是在世界中共在......独在是共在的一种残缺的样式,独在的可能性恰恰是共在的证明”。由此看来,海德格尔坚持一种坚定的共在论——此在本质上是共在,即使独在也是共在的某种样式。在这个方面,海德格尔与马克思可以会通,众所周知,马克思乃是坚定的共在论者。他表示“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在共同体(Gemeinschaft)中,个人(jedes Individum)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die persönliche Freiheit)”。这是因为个人力量(die persönliche Mächte)只有借助分工(die Teilung der Arbeit)才能转化为物的力量(diesachlicheMächte),而分工则依赖于共同体。
马克思的共在论,还表现为他对群众和阶级的高度重视。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die Waffe der Kritik)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die Kritik der Waffen),物质力量(die materielle Gewalt)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由此引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在毛泽东看来,我们要依靠群众,因为群众的数量巨大,能够充当革命的主力军;我们要为群众服务,为群众谋取利益。另一方面,“阶级”(Klasse)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是马克思理论分析的基本单位。诚如马尔库塞所言,我们分析历史实存的最终单位,不是个体(die Individuen),而是群体(Gemeinschaften)。卢卡奇也说:阶级的观点不同于并且优越于个人的观点,“个体决不能成为事物的尺度”,“只有阶级才能在行动中冲破社会现实,并在这种现实的总体中把它加以改变”。

无论是海德格尔还是马克思,都认为共在是人的基本规定——人总是与他人共在,总是生活在共同体中。这是海德格尔和马克思在共在论上可以会通的第一个表现。第二个表现是,他们都很清楚,日常的共在多半是非本真的,他们都为日常共在的非本真性而付出了理论上的忧虑和操心。在海德格尔看来,日常共在多半是非本真的,这是因为物理意义上两个物体挨到一起,物理意义上的短距离并不构成真正的共在关系。在汉语文化中,诸如“近在咫尺远在天涯”、“同床异梦”、“身在曹营心在汉”都是这方面的生动说明。同一大楼者、同一办公室者、同一房屋者未必能构成真正的共在关系,未必意味着一个真正的共同体。通常有两个极端,一种是过度冷漠、互不关心,一种是过度热心、越俎代庖,特别是“雇来共事的人们的共处(das Miteinandersein),常常只靠猜疑来滋养”。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多半还没有构成真正的共同体,所以,首要的问题并不是去考虑这个共同体为何多半是非本真的,而是要考虑这个共同体究竟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指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为了谋取自己的利益,总是在标榜自己建立了能够代表普遍利益的共同体,其实只是虚幻的共同体,只是将自己的利益标榜成共同体的利益;在虚幻的共同体(die schein bare Gemeinschaft)中,只有统治阶级内部才享有自由,对于被统治阶级而言,这种共同体不仅是完全虚幻的,而且是新的桎梏。因此,日常共在多半是非本真的,并不是因为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存在斗争,而是因为个体与虚假共同体之间存在斗争。这是海德格尔与马克思在共在论上可以会通的第二个表现。
前面提到,马克思将群众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这在欧洲哲学史乃至世界哲学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而另一个方面则是要注意教育群众和领导群众,“否则‘掌握群众’只能成为一句空话。群众就会受到完全不同的力量驱使,去追求完全不同的目的”。马克思同时也很清楚,无产阶级必须将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才能够实现无产阶级自身的扬弃(die Aufhebung des Proletariats)。卢卡奇注意到,只有当无产阶级领悟到自己的历史地位,亦即其阶级意识上升到无产阶级的水平,他们在行动中才会有统一性和凝聚力。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再去看《存在与时间》第27节海德格尔对“常人”(das Man)的批判,就会有全新的领悟:我们不可引申出海德格尔轻视群众的结论,毋宁说,海德格尔正是要提示我们,群众迫切需要思想引导。海德格尔提到演讲术通过驾驭情绪而驾驭群众,卢卡奇也曾提到通过赢得群众感情上的信任而领导群众。要注意教育群众和引导群众,这也是海德格尔与马克思在共在论上可以会通的表现。
海德格尔与马克思在共在论上可以会通的第三个表现是,尽管他们知道日常共在多半是非本真的,但是他们都致力于探索本真的共在。在海德格尔看来,本真的共在固然是罕见的,但是并不是没有。其一,如果说,越俎代庖(einspringen)不是本真的共在,那么,作出表率(vorausspringen)并且让他人学会操心、学会自由,这种共在应该是本真共在。其二,海德格尔说:“雇来共事的人们的共处(das Miteinandersein),常常只靠猜疑来滋养。反之,为同一事业而共同戮力(das gemeisame Sicheinsetzen),这是由各自掌握了自己的此在来规定的。这种本真的团结(diese eigentliche Verbundenheit)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从而把他人的自由为他本身解放出来。”“为同一事业而共同戮力”(das gemeinsame Sicheinsetzen)、“本真的团结”(die eigentliche Verbundenheit)正是本真的共在(das eigentliche Mitsein)。由此可见,海德格尔有关本真的共在,虽然语焉不详,但却是认真探讨过。马克思亦曾提到:“在真正的共同体(die wirkliche Gemeinschaft)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来源:《现代哲学》,2017年第1期,第35-42页。

丽泽哲学苑
simple living,noble thinking
荐稿邮箱:lize_philosophy@126.com
编辑:罗海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