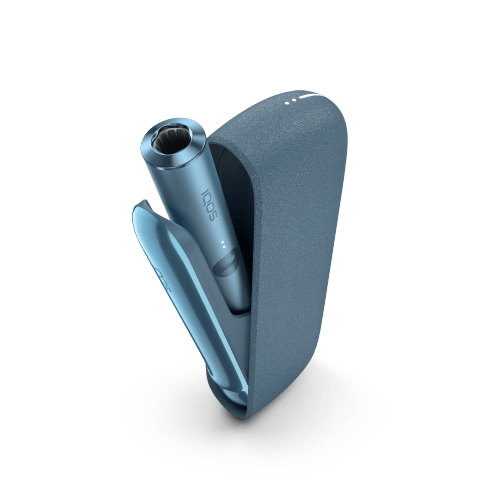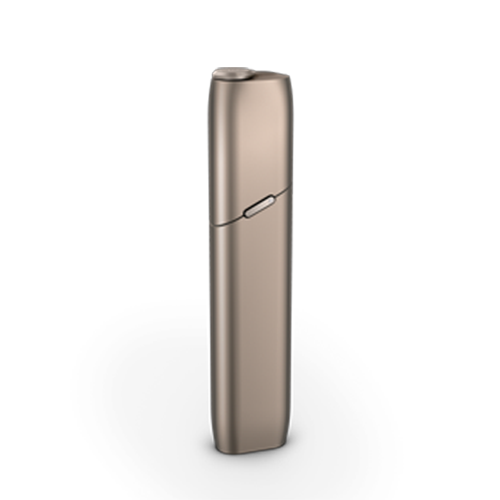“人是什么” VS “人是谁”

内容提要:对人的追问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即“人是什么?”和“人是谁?”,前者以理性或非理性的主体对人作出概念规定,并由此规定着西方哲学传统对人的理解的基调;后者视人之本质为问题而非答案。海德格尔以后一种方式通过“此在”作出对人的追问。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理解海德格尔的“此在”的前提,从此在的双重性质、此在的基本机制、此在生存的基本状态等方面对此在进行了诠释。在分析此在对理性与非理性的分歧的超越和此在对主客对立二分的认知图式的拒斥的基础上,本文剖析了近代人本主义与现代人本主义对人的理解的局限,揭示了此在的反人本主义意义,并提出海德格尔后期对此在的新的认识并未改变其通过此在作出的对人的追问的基本精神。
关键词:海德格尔/人的追问/此在/反人本主义
作者:王为理(1965.1— )男,哲学博士,现为深圳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现代西方哲学、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深圳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广东深圳 518031
来源:《福建论坛:文史哲版》2000年第03期
西方哲学传统所形成的对人的理解的基调实际上在哲学形成之日就已定下,当哲学以寻找“当存在者存在时,它们是什么”为己任、形成“这是什么?”的提问方式时,人必然被从存在者的角度去把握,人必然被以“人是什么?”的形式提问和回答。如果说柏拉图通过“理念”的确立开创了以理性认知人的传统,那么,亚里士多德对人所下出的“理性的生物”的定义则铸就了西方哲学传统对人的理解的基本模式,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西方关于人的学说,所有的心理学、伦理学、认识论、人类学都是建筑在人的这一定义的框框之内的。自古以来我们都是在从此一教条中引伸出来的想法与概念的一团混乱中过日子。”(注:Heidegger, Einfiihrung in die Metaphysik, Tü bingen: Niemeyer, 1976, S. 108.)海德格尔认为,“理性的生物”这一人的定义根本上是一个动物学的定义。笛卡尔以“我思”确立起人作为特殊主体的地位,实际上是亚里士多德人的定义的一个变种。总之,“理性”也好,“主体”也好,西方哲学传统对人的理解实际上都遵循着“人是什么?”的提问方式,提问之时就已经有了问题的答案。
但是,“对人之本质的规定绝不是答案,而根本上是问题。”(注:Heidegger, Einfiihrung in die Metaphysik, Tübingen: Niemeyer, 1976, S. 109.)要理解人,必须追问人,而不是简单地问“人是什么?”并依此问题所框定的方式给人下定义,对人作出概念的规定。那么,如何才能做出人的追问呢?海德格尔指出:“因为人作为历史性的人而是他自己,追问人的独特的存在的问题就不得不从‘人是什么?’这种形式变成‘人是谁?’这种形式。”(注:Heidegger, Einfiihrung indie Metaphysik, Tübingen: Niemeyer, 1976, S. 110.)
“人是谁?”与“人是什么?”作为理解人的两种不同方式究竟有何不同之处呢?通过对这两种不同方式的区分,海德格尔一方面对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人的理解模式作出了概括,另一方面对超越传统、探索人的追问的新的方式做出了与众不同的思考。海德格尔越过整个西方哲学传统所形成的对人的理解的“理性”、“主体”所支配的格局,回溯到古希腊思想的源头。在这一回溯过程中,海德格尔特别发掘了巴门尼德思想的意义,通过对巴门尼德的名言“To gar auto noein estin teKai einai”(但思与存在是同一的)的独辟蹊径的理解,海德格尔指出“巴门尼德的说法讲出来的东西,就是一种从存在本身的本质来对人的本质的规定。”(注:Heidegger, Einfiihrung in die Metaphysik, Tübingen: Niemeyer, 1976, S. 110.)由此入手,海德格尔视“人是谁?”的追问为“原始地吟诗”、“诗意地奠基”。通过倾听希腊人对人的存在的诗意之思,海德格尔揭示出人在“开端”(哲学产生之前)与“末尾”(即“理性的生物”成为人的定义并流传至今)的差别,“末尾显示在这个公式中:anthrōpos=zōion logon echon:人,有理性作为装备的生物。”开端则可归结为“一条自由形成的公式”:“physis=logos anthrōpon echōn:这个存在,这个起作用的现象,需要那居有并建立人的存在的采集。”(注:Heidegger, Einfiihrung in die Metaphysik, Tübingen: Niemeyer, 1976, S. 134.)海德格尔所说的“末尾”与“开端”实际上分别表征着“人是什么?”和“人是谁?”两种不同的理解人的方式,在末尾处人被外在化为某种能力,而这种能力建立在特种生物的现成状态之上;在开端处,人的存在建立在存在者的存在之敞亮(Erflnung)中。因而,在海德格尔看来,“人是谁?”之间代表着对人的一种“真诠释”,这种诠释从根本上对人的问题上的习惯的看法提出疑问,这种诠释代表着一种视线,这一视线“全然不指向有待于视之处”,因而它根本不会去追究“人是什么?”这样,西方哲学传统所形成的对人的各种各样的理解都是与人之间格格不入的,人之间必须采取一种全新的方式,而这一全新的方式早已孕育在西方哲学的开端之中,“就在西方哲学的开端,已经很明显的是,存在的问题必然包含此在的根基。”(注: Heidegger, Einfiihrung in die Metaphysik, Tübingen: Niemeyer, 1976, S. 133.)因而,海德格尔经由“此在”进入“人是谁?”之问。
在对此在的分析中,海德格尔在对“生存论性质”(此在的存在特性)与“范畴”(非此在式的存在者的存在规定)作出严格区别的基础上指出:“与这两者相应的存在者所要求的发问方式一上来就各不相同:存在者是谁(生存)还是什么(最广义的现成状态)。”(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6页。)显然,这确立了海德格尔通过此在对人做出追问的方式是“人是谁?”而非“人是什么?”但这一追问是如何实现的呢?因而我们必须进入对海德格尔的“此在”的诠释。
“此在”(Dasein)是《存在与时间》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也是海德格尔之思中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单从Dasein一词的中译情况就能感受到这一点。到目前为止所见的译名有:“亲在”、“人的存在”(混然中处的在者之在)、“此在”、“本是”、“存在者”、“此有”、“缘在”、“现前存在者”或干脆将Dasein直接拿来。这一众说纷纭的状况表明要在汉语中找到一个符合“信、达、雅”标准的Dasein的对应词是多么困难。(注:最大的难处在于,“Da”在德文中既可以指“这里”、“这个”,又可以指“那里”、“那个”,只要在汉语中能找出一个这样的代词,即既可近指又可远指的代词,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据《汉语大字典》,“若”字作代词用时,既可用于近指,相当于“这个”、“这样”、“这么”,又可用于远指,相当于“那”、“那么”。“若”字能否用来译“Da”?暂存此一问。顺便说句,到目前为止的一切意译“Dasein”一词的企图都显得左支右绌,总是只能反映其中一方面的内涵,有些译法不是显得牵强附会,就是只能徒增理解的混乱,至于将“Dasein”直接拿来,亦非长久之计。我在本文中之所以仍选用“此在”这一译名,主要是考虑到虽然“此”也无法涵盖“Da”之所指,但相对而言,译为 “此在”尚未流失“Dasein”的丰富内涵并为对“Dasein”的解释保留了较为丰富的可能性。但是“此在”这一译名将来必将为更好的译名所取代。)在此我无意对这些译法做出详尽的评说,我想指出的是:
第一,在把握“此在”时,我们必须考虑其“克服形而上学”背景。此在是《存在与时间》中的基本概念,也许是由于海德格尔有过“此在的形而上学”之说,有人认为此在仍然是一个形而上学概念,甚至仍然是一个主体形而上学概念。但我认为,此在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克服形而上学的“路标”而出现在海德格尔之思的“林中路”上的。第一章对海德格尔之思的克服形而上学的大思路的分析,是我们把握“此在”的基础。
第二,我们必须记住,此在作为具有优先地位的存在者是海德格尔凭以窥视存在的意义的窗口,也就是说,此在的分析是进入存在的“准备性分析”,谈Dasein,必须与Sein相关,这就要求,一方面不能离开Sein去谈Dasein的优先地位、意义、结构等,另一方面又不能将Dasein等同于Sein。而这又进一步要求我们对“存在是什么?”( Was ist dasSein?)中的“是”(ist,在)有所领悟, 形而上学恰恰迷失于这种追问,简单地视“ ist ”为系动词“是”并进而得出“存在”(das Sein)就是“存在者”(was)的结论。对形而上学从“是”(ist)动词引伸出“sein”的意义的这种做法海德格尔是持批判态度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将“sein”理解为“是”并将这种理解带入对“Dasein”的理解。 从中我们应该领悟出的是,“sein”不是“什么”,Dasein是sein在生成中绽出到时而显现的某种存在状态,而这就要求阻断Dasein 与sein的实体性同一的可能。
第三,无论如何,海德格尔用Dasein是谈论人的,但我们为什么不能简单地将Dasein等同于“人”或直接将其译为“人”呢?选定人这个具有优先地位的存在者作为揭示存在的意义的突破口时,海德格尔不得不面对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人的概念,为了逃避这个传统中的“人”,海德格尔费尽心机,选用了Dasein一词。对海德格尔不用“人”而畅论人的存在的这一标新立异之举,威廉·巴雷特有过一句十分到位的评论:“海德格尔能够说出他想要说的关于人的存在的一切而既不用‘人’也不用‘意识’,这意味着在主体与客体之间,或者说在心灵与肉体之间曾经为近现代哲学挖掘出来的鸿沟,要是我们不挖掘的话,本来是没有必要存在的。”(注: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段德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30~231页。)巴雷特的话对我们理解“此在”具有启发性。
在以上的理解前提下,我们展开对海德格尔以此在对人所做出的追问的诠释。首先我们应当弄清的是海德格尔以此在指什么,而要做到这点我们又得明白,虽然“存在论差异”在《存在与时间》中并未被十分明晰地提出,但“存在”与“存在者”的关系已经得到明确的论述,存在是存在者之被规定为存在者的那个存在,但“存在者的存在本身不‘是’一种存在者。”(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8页。)此在是一种存在者, 但与其它存在者不同,这种存在者“除了其它存在的可能性外还能够发问存在”,(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0页。)这种存在者就是我们自己向来所是的存在者。因而“对存在的领悟本身就是此在的存在规定,此在作为存在者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存在论地存在。”(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6页。)海德格尔以“此在”来指称人,实质上是在强调人的存在论的天职,即人开显存在的意义的能力。
此在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这种存在者的‘本质’在于它去存在(zu—sein)。”(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2页。)海德格尔之所以在本质一词上打上引号,意在打破西方哲学自中世纪以来的 essentia ( 本质)与existentia(存在)的二分,进而标明:(1)此在不是一种现成存在,此在的存在在于它的生存(existenz),此在的存在方式因而与其他存在者的存在方式根本不同;(2)此在就是它的可能性, 此在的各种性质对此在来说总是去存在的种种可能方式,而不能理解为现成存在者的现成属性;(3)因而,此在“并不表达它所是的什么(如桌子、椅子、树),而是表达存在。”(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3页。)此在没有它的可被概念规定的本性。另一方面,“这个存在者为之存在的那个存在,总是我的存在。”(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 王庆节译, 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3页。)海德格尔在此除了进一步标明此在不能把捉为某种现成存在者,此在总是作为它的可能性来存在之外,还预示出:(1)此在的向来我属性(Jemeinigkeit)与此在的基本机制“在世界之中存在”相关,此在就是在世界之中存在,世界总是与此在联在一起;(2)既然此在本质上总是它的可能性,它就既可以在其存在中选择自身,获得自身,也可以失去自身,因而此在的向来我属性规定了此在存在的本真状态和非本真状态两种样式。
由此在的双重性质的准备性分析入手,海德格尔揭示出此在的基本机制是“在世界之中存在”。这就是说,此在不是一种孤立的、单独的存在,它总是处于世界之中,而“在世界之中”并不意味着此在与世界的空间关系,而是指此在与世界处于一种不可分割的浑然一体之中。“世界”也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客观世界,“‘世界’在‘在世界之中’这个规定中的意思根本不是一个存在者,也不是一个存在者的范围,而是存在的敞开状态。”(注:Heidegger, Wegmarken,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1978, S.346.)
在世界之中存在是此在的一项无法逃避的存在论上的事实。此在的这一事实性(Faktizitat)(注:海德格尔以Faktizitt 指具有此在性质的存在者状况,以Tatschtigkeit 指一般的现成状态的存在者的存在状况,二者是相区别的。)表明,此在在它的“天命”中已经同那些在它自己的世界之内昭明的存在者的存在缚在一起。此在的事实性与此在就是其可能性形成了此在结构上的一种张力,可能性凸显了此在的自由及开显世界义蕴的主动性,事实性则标明了此在的“被抛入性”(Geworfenheit)。这个“被抛入性”渗透着此在本身,一方面此在无法掌握自己的起源,另一方面此在注定与存在者相关,注定在本质上依赖于存在者。
海德格尔的此在存在的事实性、被抛入性实际上揭示了人的有限性,在《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中,海德格尔进一步分析了人的有限性问题。海德格尔指出“在基础本体论这个名称下面就包括了作为使理解存在可能的决定性因素——人的有限性问题。”(注:Heidegger, Kant and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 Translation by Ricard Taft, Indianapolis: Indiana Vniversity Press, 1990,P.162.)因而,有限性规定着人的本质,并将人与存在的理解关系突现出来。由于此在与非此在式的存在者之根本不同,此在的有限性不能理解为物质对象的时空限度,此在的有限性与人的存在的基本状态相关。人的存在是有限的,因为人的存在弥漫着非存在。当此在作为存在着的存在者而“畏”、“死”时,非存在的“无”在人的存在中展开,人的有限性在此在的存在与不存在之中显现。
此在在世的基本机制决定了此在无可逃避地共属于它的世界,无可逃避地与他人共在,海德格尔称之为此在的“日常的杂然共在”。在这种杂然共在中,人本质上从属于他人之列,这样的“他人”就是“众人”(das Man)。这个“众人”指定着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即为“平均状态”而存在,此在在杂然共在中任众人摆布。海德格尔把此在日常藉以在此的基本方式称为“沉论”(verfall),其基本样式是闲谈、 好奇、两可,此在从它自身脱落,即从本真的能自己存在脱落而沉沦于“世界”(注:海德格尔用加了双引号的世界表示能够现成存在于世界之内的存在者的总体的世界,即通常意义上的客观物质世界。),混迹于靠闲谈、好奇、两可来引导的杂然共在之中,消失于众人的公众意见之中。海德格尔称之为此在的非本真状态(Uneigentlich Keit)。此在在沉沦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引诱、安定、异化和自拘之中“从它本身跌入它本身中,跌入非本真的日常生活的无根基状态与虚无中。”(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16页。)
通过对沉沦的描述,海德格尔揭示出了此在生存的两种最基本状态。在非本真状态中,此在不立足于自己本身而以众人的身份存在,失本离真;在本真状态(Eigentlich Keit)中此在立足于自身生存。对海德格尔的这一立论,我们应从如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第一,海德格尔一再表明,沉沦也好,非本真与本真也好,所谈论的不是道德问题,不包含道德评价的成份,其立场是价值中立的,是在生存论存在论的维度展开的,所阐释的不是关于“人性之堕落”之类的任何存在者状态上的命题。
第二,沉沦作为一种“在之中”的存在方式为此在在世的基本生存论状态提供了最基本的证明。此在的非本真生存表明正因为领会着现身在世,此在才能够沉沦,这反过来表明“本真的生存并不是任何飘浮在沉沦着的日常生活上空的东西,它在生存论上只是掌握沉沦着的日常生活的某种变式。”(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17页。)
第三,就非本真生存与本真生存的关系而言,一方面非本真性以本真性为基础,只有当此在就其本质而言可能是本真的、即拥有本己的存在者时,它才可能失去自身,这是就此在的存在论层面而言,另一方面非本真状态“可以按此在的最充分的具体化情况而在此的忙碌、激动、兴致、嗜好中规定此在”,(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4页。)本真生存其实是在非本真生存基础上的一种转化或者说是某种变式。
第四,非本真生存是此在在日常生活中的常态,而本真生存则有待于此在自身的觉醒。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日常生活中盲目从众的非本真生存虽然在结构上以事实性为根基,但在沉沦中此在只能背弃、遮蔽其本真的可能性,却不能取消它,因而就此在的存在性结构而言,转俗成真永远可能。另一方面,此在虽然可以通过“决断”(海德格尔晚期改提为“一切放下”(Gelassenheit)将本真的自我从“他人”或“众人”的存在模式中拯救出来,但“在世界之中存在”作为此在基本的构成状态,却不会因此取消,也就是说,即使是本真的生存,它在体现其自身存在论的天职中,也必须通过当前的“情境世界”才能够让自己“存在于此”。(注:参阅袁保新:《尽心与立命——从海德格尔基本存有论重塑孟子心性论的一项试探》,见《孟子思想的哲学探讨》,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5年印行,第179—180页。)
第五,由于此在的存在机制包含着沉沦,“依照此在的存在机制,此在在‘不真’中”,此在的实际状态中包含有封闭状态和遮蔽状态,就其完整的生存论存在论意义来说,“此在在真理中”这一命题同样原始,也是说,“此在在不真中”。(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67页。 )这表明此在相应于“存在”而言的澄明与晦暗、显露与遮蔽的二重性。
从对此在的诠释中我们可以看出,海德格尔对人做出了与众不同的追问,这一人之问具有什么意义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考察海德格尔通过此在有无破除西方哲学传统中形成的对人的理解的“理性”和“主体”的经典概念。这一考察是对此在的继续诠释,也是对海德格尔的人之问与近代人本主义和现代人本主义对人的理解的差别的揭示。
近代人本主义以理性理解人,现代人本主义不满足于近代人本主义对人的理性解释,从非理性层面对人做出了新的理解。海德格尔之思与现代人本主义具有相同的背景,但海德格尔走的是一条不同的路。在海德格尔看来,“人的本质在于,人比单纯的被设想为理性的生物的人要更多一些。”“与从主观性来理解自身的人相比,又恰恰更少一些。”(注:Heidegger, Wegmarken,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1978,S.338.)一方面,理性并不能反映出人的全部,对人需要有“更多一些”即更本源性的理解;另一方面,近代人本主义突出的是人的主观性,其实质是畸形膨胀了的人的理性主体性,与之相比,真正的人应该“更少一些”。克尔凯戈尔一反近代人本主义的理性模式,以“孤独的个体”理解人的存在,凸现出人的非理性层面,并以之作为排斥理性的根据,但现代人本主义的这种做法并不能真正解决人的存在的问题。“非理性主义唱的是理性主义的对台戏,理性主义盲目以待的东西,非理性主义也不过眄顾而言罢了。”(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67页。)这是因为,“非理性主义只是理性主义公开化了的弱点与完结了的不灵,因而本身就是一个非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是从理性主义中逃出的一条出路,这条出路却不引向自由,而只更多地缠结到理性主义中去了,因为此时唤醒了一种意见,认为理性主义只消通过说不就被克服了,其实它现在只是更危险了,因为它被掩盖而不受干扰地唱它的戏了。”(注: Heidegger, Einfiihrung in die Metaphysik, Tübingen: Niemeyer, 1976,S.136.)与近代人本主义和现代人本主义不同,海德格尔来了个釜底抽薪,通过以“此在”所做出的人之问彻底跳出了理性与非理性的纷争。此在既不能归结为“我思”式的理性的人,也不能归结为“孤独的个体”式的非理性的人。
之所以如此,决定性的因素在于此在具有根本不同于主体概念的内涵。现代人本主义之所以仍然停留在传统哲学范围之内,未能真正克服对人的理解的理性模式的局限,根本原因在于现代人本主义在对人的非理性的理解中所确立的仍然是作为主体的人。通过对主体这一经典概念的破除,此在对人做出了新的理解。
首先,此在的基本机制表明,此在与世界并不是两个不同的相互对立的存在者,此在与世界的关系不能理解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主体和客体同此在和世界不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4页。)近代人本主义的作为理性主体的人和现代人本主义的作为非理性主体的人都是人为设定的、孤立的、与世界相分离的人,因而都未能对人作出正确的理解。
其次,此在“在世界之中”,即此在在世,本质上就是“烦”,烦是此在在世的基本结构,作为一种本质上不可分割的处于整体性中的生存论的现象,烦不能理解为人因某种特殊的行动或欲望等而产生的忧烦心理或情绪。海德格尔从此在被抛入世,与世内存在者打交道的两个方面剖析此在之烦:“寓于上手事物的存在可以被理会为烦忙,而与他人的在世内照面的共同此在一起的存在可以理会为烦神。”(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 233页。)一方面,此在在世因与他物打交道而烦忙,此在与其使用的用具发生关系而与他物相关,构成“周围世界”,表明此在与他物不可分离,“无世界的单纯主体并不首先存在,也从不曾给定。”(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3页。)另一方面,此在在世因与他人打交道而烦神,此在因而与他人相关,此在在世不是孤独的个人的在世,而是与他人一道共同在世,从而构成“共同世界”。这表明“无他人的绝缘的自我归根到底并不首先存在。”(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3页。)海德格尔剖析此在在世的基本结构的主旨在于, 他不愿预先设定一个孤立的主体,然后把一个个孤立的他人或他物附加到这个主体之上。近代人本主义的谬误正在于首先将人从存在的整体中抽象、分离出来作为主体,然后再去论证、认识与之相对立的客体,去建立所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现代人本主义式的“孤独的个体”则干脆在对人的主观性的特别强调中将人与他人、人与世界彻底割裂开来。
最后,烦作为此在在世的基本结构是由“畏”显示出来的。畏与“怕”有根本区别,怕指向某种确定的存在者,怕之所怕者是某种确定的、具体的危害和威胁,它只是此在在存在者状态上的现身方式,而“畏之所畏者不是任何世内存在者,因而畏之所畏在本质上不能有任何因缘。”(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25页。)畏是没有任何确定的对象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说:“畏启示着无。”(注: Heidegger, Wegmarken, Frankfurtam Main: Klostermann, 1978, S. 111.)畏显示的不是任何具体的东西,而只是无。畏所启示出来的这种无的境界正是“在世”本身,因此畏作为此在的现身方式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即此在在其中的世界展开开来,此在的存在也因而得到了揭示。近代人本主义对人的理解根本上就没有达到这一深度,现代人本主义中,克尔凯戈尔对人的畏惧现象做过深入的探讨,海德格尔认为“在对畏的现象分析中向前走得最远的是索·克尔凯戈尔,不过这一分析是在对与神学相关联的原罪问题作‘心理学’的解说时进行的。”(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30页。 )在对畏的带有神学背景的体察中,克尔凯戈尔主要表明了畏惧是对人的个性的一种磨炼,畏惧使人的生命个体化,海德格尔则将对畏的揭示引向无,并在无的背后展露出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人因此再也不被理解为一个个自我封闭的“孤独的个体”,人本来就在其自身之外,人与世界本为一体。正是在此基础上,海德格尔进一步揭示了此在的最本己的、无关涉的、不可超越的、不确定的可能性的“死”,在此在的“向死而在”中显现出此在的完整的、本真的生存,并进而将此在的存在的意义理解为时间性,使此在的存在在时间中展开,从而揭示出人的存在的有限性和人的存在的深刻的历史性。
总之,通过此在对人的追问,海德格尔摧毁了“我思”这个解释世界的出发点,“我在”即此在成为揭示存在的秘密的钥匙。这样,作为主体的人的优先地位被否定,“我思故我在”的传统被推翻,现代人本主义对人的非理性解释也相应地被摒弃,人被从西方哲学传统即形而上学传统、人本主义传统中的“主体”地位还原为“提出存在的问题的存在者”的原有身份。具体来说,“此在”的意义表现为:第一,此在突破了追问人的存在的“人是什么”的传统方式,人的存在不再被描绘为以理性为核心的精神性存在,也不再被理解为非理性的个人的情绪体验,理性与非理性的分歧被超越。现代人本主义中克尔凯戈尔通过强调人的存在所面临的或此或彼的选择的意义,在改变人的追问的方式上做出过有益的尝试,但只有此在对人的存在的整体结构的把握才真正改变了哲学的提问方式,人再也不是从作为“什么”意义上的存在者的方面去理解了。第二,通过对此在的基本机制“在世界之中”、此在在世的基本结构“烦”以及“畏”、“死”以及此在的双重性质、此在在世的基本状态的揭示,海德格尔摒弃了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主体观念,拒绝了人本主义的主客体对立二分的认识图式,孤立的主体被消解,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之间的鸿沟被填平,人既被从抽象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中解救出来,又避免了成为克尔凯戈尔式的孤独的、与他人、世界隔绝的个体。第三,由此在展开的对主体形而上学的批判一直影响着海德格尔之思,晚期海德格尔所表现出的对以主体征服客体方式对待世界的危险性、对人的活动的全球性后果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特别关注,是与海德格尔以此在对人的理解密切相关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海德格尔提出的“此在”以反人本主义的形式提出了人本主义发展中所必然面对的课题。第四,海德格尔通过此在所做出的人之问,摒弃了人的问题上的所有宗教和超验的东西,通过此在,海德格尔描述的是一个上帝不在场的世界,这清除了对人的理解的异化形式。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通过人之问,海德格尔揭示了人的有限性问题。通过对人的有限性的揭示,海德格尔割断了西方哲学传统包括神学传统所强加的诸如上帝之类的一切超越性的东西与人的联系,在海德格尔那里,人是不能通过对某个超越的、无限性的实体的肯定来取得无限性的。牟宗三先生认为海德格尔“只执定于有限性”而不知“人虽有限而可无限”,(注:参见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见黄克剑、林少敏编:《牟宗三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427页及其以下。)实际上, 海德格尔恰恰通过对人的有限性的深刻揭示,在人的存在中展开了非存在的“无”,从而达到了人的非实体性的无限。
当然,此在是否准确把握了人,人的存在是否就此被昭明,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晚期海德格尔思想的变化反映出海德格尔对此在的重新认识。随着从“存在”到“本然”、从“决断”到“一切放下”、从“此在”(Dasein)到“此—在”(Da—sein)的变化,在晚期海德格尔之思中,此在从具有优先地位的存在者退居为“天、地、神、有死者”四方游戏中的一方。但我以为,在这些变化中,海德格尔通过此在所做出的人之问的精神不变,此在的反人本主义意义,此在所寻求的对人的实体性、人的二元性的破除,此在对人与世界、人与自然、人与存在的圆融境界的体认贯彻着思之全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