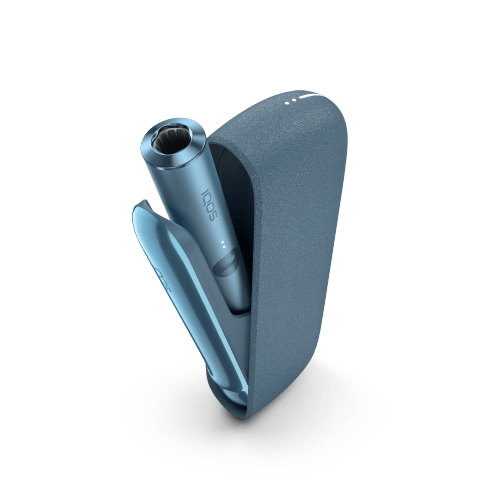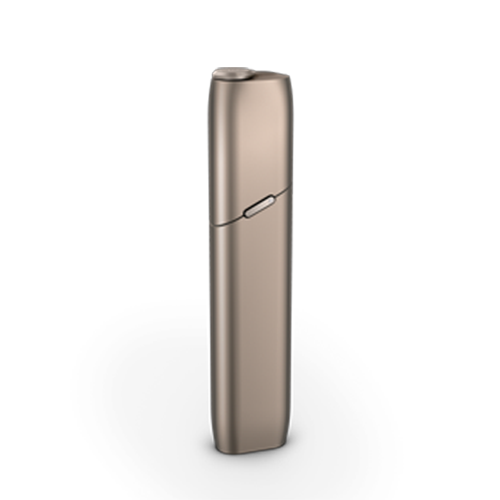南哲思享 | 张荣:奥古斯丁对古典自然法的改造及其意义
自然法是西方哲学传统的核心概念之一,它经历了古典时期、中世纪和近代三次重要演变。研究自然法概念不仅对理解西方宗教、道德和政治法律思想的演变有重要意义,对理解西方哲学本身也有非同寻常的价值。奥古斯丁虽没有成熟的自然法理论,但他对永恒法与世俗法的区分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一区分不仅对古典自然法思想是一次革命性转换,更对托马斯自然法思想的形成有奠基之功。
摘要



自然和自然法密不可分,对自然的不同理解规定着自然法的不同内涵。按照哲学历史词典的解释,表述自然法概念的拉丁文术语有两类:自然法(ius)和自然法则(lex),ius有法、权利与正义之义,lex有法律、律法(或律)含义。前者又分为自然的法(Ius [Recht] naturae)和自然性的法(ius [Recht] naturale),相应地,后者分为自然的法则(法律或律法)(lex [Gesetz] naturae)和自然性的法则(lex [Gesetz] naturalis)。德语中的Recht常被例举以对应于拉丁语的ius,似乎与lex无关,前者侧重正确、正当或正义之含义,偏主观判断,而后者lex偏重客观法则,外在的法律(律法)或客观条文、章程。在我看来,德语的Recht这个词之所以难译,不仅因为它同时涉及ius和lex两者,既具有主观的含义,也具有客观外在的含义,而且因为自然法(Recht)作为最普遍的ius,其含义异常丰富,因为与之对应的自然概念本身就有多样性内涵。
一、古典的自然概念与自然法
按照《哲学历史词典》,自然法的概念史含义可以参考其与自然概念的关系进行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关系。
谁把自然看做本质特性,自然法就是个体的或集体的生存法(Daseinsrecht);把自然看做本源性之物,自然法就是元秩序;谁把自然看做真正不可朽坏的,那自然法就是整体之状态(status integritatis);谁把自然看做因果性,自然法就是自然法则(Gesetz);谁把自然看做合理性,自然法就是理性权利(Recht);谁把它看做观念性(Idealitaet)(精神本性[Geistnatur]),自然法就是法的观念(Rechtsidee);谁把自然看做实在性(Sachnatur 物性),自然法就是物的自然(权)(Natur der Sache);谁把它看做受造本性,自然法就是受造世界的秩序(Schoepfungsordnung);谁把自然看做单纯的活力(Vitalitaet),自然法就是最强者的权力法(Machtrecht oder Masse),它包含有社会性——时代正义;而且有保守的或革命的含义区分。法(Recht)就是秩序(客观性的法),由此推出:自然法(lexnaturalis)乃是立法的学说体系或范型;法(Recht)是要求(主观性的法),由此推出:自然性的法(iusnaturale)就是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总体或者相较于国家的人格性权利(Persoenlichkeitsrecht)。法被看做是实证的(严格意义上的)法(Recht),由此推出:自然法就是衡平法(iusaequum);当法(Recht)意愿正义时,自然法必须是法的绝对有效的形式“理念”或一种相对有效的实在理想;当法致力于单纯的“益处”时,自然法就是个人或社会福祉的规范;当法只应该保障安全时,自然法就是权利保护的保障;当法被看做“传统”时,自然法就恰恰指“古代法”(altes Recht);当法喜欢为人性(人道)服务时,自然法就是人权总体。
总之,ius即正当,包含权利、主权,偏主观和理性,权利学说。lex即法律,包含自然法则、法,偏客观、自然(恩典,超自然),重他律、强制、义务。它们的共同点是普遍、绝对与约束性,正义性和效力性。
在古希腊早期哲学中,自然(physis)概念与本质(性状)与变化(生长)紧密相关,和本原相关。它蕴含两层含义:自然存在者及其本质(本原,开端与归宿);变化和生长的规律。简言之,自然意味着自然存在者及其本质、规律。在巴门尼德的存在学和真理论中,自然不再有如此基础地位,自然只属于意见范畴。巴门尼德之后,从元素论到原子论,自然再一次被重视,被看做变化着的事物的原则-本原和元素、万物真正的本质和实体性本原。德谟克利特在宇宙论和人类学-伦理学意义上谈论自然,原子和虚空不仅是一和多的统一,而且是客观和主观的统一,这个变化非常重要。自此,自然概念的哲学意义开始涌现,进而过渡到了古希腊哲学的新阶段——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自然开始真正和法则(nomos)关联。
与此同时,“自然禀赋”这一概念也开始出现,灵魂和精神也进入自然之中,人类学,伦理学,教育等都和自然紧密联系了,本性、第二自然的概念开始孕育、成长起来。人的天赋和后天训练紧密相关,形成规范,医学上讲的自然和不正常状况都是在自然力的意义上得以被强调。人的体质、天资问题都是自然禀赋,兼具物理意义上的和心理学意义上的含义,自然和本性结合。比如智者派就是这样,把自然和内在规则(nomos)看做一个对子。自然的神圣性也开始被强调,貌似外在的nomos其实是人设定的规则。自然的本质(Wesen)和公共的本质(Wesen)合一,道德的和宗教的以及审美价值都建基于人的设定(Satzung 章程)。和自然相比,法则(nomos [Gesetz])是主观的、可变的。自然法的两个要素里面,一个是客观神圣的,一个是主观人为的。但是,在普罗泰格拉那里似乎也已包含了这样的思想:普遍有效的法(Gesetze Recht])应该是诸神给与的。人不行,神可以。神是万物真正本质(自然)的缔造者。自然是真正的本质,自然法不是一个形容词意义上的偏正词组,因为这与正义、不义相关。
智者派是一个枢纽,不仅是自然概念的一个枢纽,也是自然法概念的一个枢纽。斯多亚派的社会的和理性的意义上的自然法,更强者的自然法的习俗观念都可以从智者派那里找到其根源。除了神圣的自然力这个含义外,智者派(在柏拉图对话中)的自然概念还有一个教育学上的重要含义:自然资质(Anlage)、练习和教授之间存在一种内在关系。尤其是,练习和教授被看得比天生的(angeboren)自然还要高一个层级,人可以通过练习比通过自然资质(天赋)变得更能干。教育被看做是首要特征,自然天资相比与教育,处于次要位置。优异(Arete)是可教得的。柏拉图在早期的伦理对话中就坚持了智者派的观点。好的自然天资里的这个自然也具有教育、伦理与人类学含义:“身体的性状,体质,物理的状态,性状,甚至精神的资质,某些精神态度和资质。”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和《政治家篇》里仔细分析了自然和习俗之间的对立。针对更强者的自然法,柏拉图提出了一个真正的和本质上的正义构想(正义理念)与之对立。心灵更高级的理念秩序——是真正的人的法则的基础——是真正的自然性之物。
柏拉图总体上贬低自然,抬高技艺(techne),抬高灵魂,如果自然是一切生产变化的开端和原则,那么,灵魂作为自己本身并从自身出发运动的东西就是整个自然的运动和生命原则。在这个意义上,灵魂就是真正的和本己的自然原则(原理)。世界灵魂就是整个自然。但得穆革(造物主)在世界灵魂之上,它为世界整体的秩序与和谐操心。它象征神圣的灵魂,但如果它不能指向永恒的真正存在的理念,就不能是世界秩序与和谐的原因。善的理念就是目的性秩序的原因。当然,柏拉图把理念、本质、自然看做一样的东西。他是在理念论意义上讨论自然的。亚里士多德是调和的,自然观也一样。他把自然理解为物质实体、本质和变化,看做运动、灵魂与原则。
斯多亚和伊壁鸠鲁派则更多地以伦理视角看待自然,看做一种合乎自然的生活理想。整个自然(All-Natur)就是普遍自然。神的逻各斯就是自然的普遍的逻各斯。神圣的世界法则(规律,自然即命运)。自然和人的技艺的对立在此得到了统一。在柏拉图,技艺高于自然;在亚里士多德,自然高于技艺(秩序论)。自然和技艺的对立在斯多亚神圣的世界根据(Weltgrund)中被扬弃了。人的合乎自然的伦理态度(Verhaltung 行为)不得不指向肉体与灵魂的人之自然的目的论秩序,不仅与德性相关,而且也与单纯的命运有关。伊壁鸠鲁哲学的关键是快乐,合乎自然的快乐,因而是一种幸福主义的伦理学。国家和法都建立于人的和谐一致。既没有什么来自自然的人之中的共同体,也没有普遍有效的自然法,因为偶然的理性,也因为原子的倾斜运动。
总之,古典自然法的实质在于:普遍性(普世性)、绝对性和个体化。这是古典希腊自然法思想萌芽的发展结果,是古罗马西塞罗法律思想和基督宗教法律思想的共同根。这样一来,古典自然法就从古希腊鼎盛时期的“知识正当”发展为古希腊晚期的自然正当(ius, righteness, Gerechtigkeit),这一跳跃直接和中世纪的自然法就牵系起来了。



二、奥古斯丁论自然与永恒法
中世纪的自然(Natura)概念主要表达实体、本性与自然物。与古代自然概念相联系也相区别。中世纪的自然概念更多和创造与受生、给予与被给予相关。我们在此结合奥古斯丁的文本进行分析,就可以发现,他的自然观对中世纪自然法思想具有奠基性意义。
奥古斯丁接受了古典哲学传统的那种自然观。他认为,“自然(natura)无非是这样的东西:人们正是透过它认识到,某物是以自己的方式存在的”(ipsa natura nihil est aliud, quam idquod intelligitur in suo genere aliquid esse)。也就是说,自然是真实存在的东西(res),这种东西,我们可以通过其现象认识其本质。也就是说,自然和本质(essentia)和实体(substantia)可以等量齐观。无独有偶,奥古斯丁在《论自由决断》(De libero arbitrio)第二卷末尾一节中也说过:“你知觉、理解,或以任何方式知道的每一善事,都从上帝而来,因你所遇的任何自然都是从上帝来的。”拉丁文是:Ita enim nulla natura occurrit quae non sit ex Deo. 直译就是:“因此这样一来,人们所遇到的自然,无不从上帝而来。”类似的表达出现在本节另一处:“但一切善都从上帝而来,所以一切自然无不是从上帝而来。”对应的拉丁文是:Omne autem bonum ex Deo: nulla ergo natura est quae non sit ex Deo.
仔细辨析奥古斯丁《论自由决断》中的这两个文本,非常有意思。他一方面把实际遭遇(发生)(occurrit)的自然物(res)看做实在的存在(是),也就是实体,自然即实体。奥古斯丁在这一点上和古希腊自然观一致。另一方面,他又把这种实体看做源自上帝的本质,因而是善的,把来自上帝的自然和来自上帝的善看做本质同一的。自然、本质和实体之所以能够被等量齐观,皆因为上帝这个原初根据。自然是现象,上帝才是本质。因此,被我们认识其本质(essentia)的实体(substantia)的自然物(res),是我们直观上帝的媒介和现象。在某种意义上说,上帝也是自然,只不过不是受造的,而是创造的自然。这一点直接影响了后来的爱留根纳,后者缘此对自然进行了四重区分。自然物体,在时空上具有可变性,作为灵魂的自然在时间上可变;作为神的自然,在时空上都是不变的,都是自然,自然的秩序经历了由可变到永恒的过程。到最后,作为上帝意志的自然——意愿(voluntas)取代了古希腊自然观中作为物的形成和变化原则的自然。自然就是一本书(隐喻),自然是上帝启示的工具。上帝的意志就是每个受造物的自然(本质和本性)。
可以看出,奥古斯丁(包括整个中世纪早期)把自然追溯到上帝意志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方面,是对自然的价值评估:一切自然(包括实体)本身都是善的,恶不属于自然,不是实体,只是善的缺乏(privation boni);另一方面,不管在法则(自然法则)的内部还是外部,在自然和超自然物之间,在形式上看,并无区别。自然和上帝的意志行动之间产生了关联。自然物及其法则都是按照上帝的意愿被创造的,而这种自然观直接体现在奥古斯丁的永恒法思想中。
我们知道,奥古斯丁的永恒法概念源于他对原罪的哲学阐释,尤其体现在他对属世的法律(世俗法)和永恒法的区分中。在《论自由决断》第一卷中他指出:“本来公正但可以在时间流转中公正地修改的法律称作属世的”,也即世俗法(或人法),而他把与此相对的永恒法叫做“最高理性(summa ratio)的法律”,它是“属世的法律得以正当制定又正当地更改的法律,是因之恶人得苦难,善人得幸福的法律。”世俗的或暂时的法律之所以是公正的,能被称作是法律,都因为“它导源于永恒法”。关于永恒法的意义,奥古斯丁界定为:“印在我们心中的永恒法,它是这样一部法律,根据它,万物得以完美地安排乃是公义。”不仅自然的秩序由永恒法掌管,人的全然有序也和永恒法密不可分。“因此,当理性、心灵或精神控制着灵魂非理性的冲动(libido,cupiditas 贪念)时,人就正是由那应该掌管的东西,依据我们已发现为永恒的法律掌管着。”很显然,奥古斯丁坚持了新柏拉图主义的秩序论原则,认为自然的秩序和人的灵魂秩序是一致的。遵循永恒法的人就是全然有序的人,因而是智慧的人,永恒法授权心灵控制贪欲。奥古斯丁认为心灵的这种秩序是自然的秩序,因而是符合正义的。
然而,驱使心灵做了贪欲之奴隶的,既不可能是来自上帝的自然,不论它是实体,还是本质,也不能来自他人的意志,更不会来自比心灵更高的上帝,而只能来自心灵自己的意志和自由决断(voluntas et liberum arbitrium)。正因为如此,人的罪恶(做贪欲的奴隶)受罚才是正义的。无人能强迫灵魂做贪欲的奴隶,它一定是自愿的;灵魂该受惩罚,若它自愿屈从贪欲的话。奥古斯丁把人的心灵自愿屈从于贪欲,做贪欲的奴隶,又概括为忽视永恒之事。
“恶行无非就是忽视永恒之物,即心灵靠自身便可知觉享有,而只要它热爱便不可能失去的永恒之物,反倒去追求属世之物。”热爱永恒事物而幸福的人,生活在永恒法之下,而不幸的人则服从世俗法。人有两种爱,就遵循两种法律,从而也就有两种生存。这是奥古斯丁区分世俗法和永恒法的真正意图所在。
不过,奥古斯丁也并非完全忽视世俗法的正当性,就如同他也没有完全否认希腊四枢德(明智、节制、勇敢和正义)的德行意义一样。他认为,热爱属世之物的人之所以有罪,是因为做了贪念的奴隶,而不是做了属世之物的奴隶。他始终强调,意志和意志的自由决断才是罪恶的起源和秘密所在。因此,他也肯定了世俗法的正当性。他认为,世俗法要求人们拥有那些东西,得依照保持和平、维护社会的法律。属于这些可变的属世之物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这样一些善,如肉体,以及与之有关的健康,灵敏的感官,力量,美丽等等;其次是自由,即当人们因为没有别人是其主人而自认为是自由的,以及当人们渴望脱离其主人而获得自由时,心里所想的那种自由(主观的自由感)。第三是父母、兄弟姊妹、配偶、孩子、邻居、亲戚朋友,以及任何与我们有必要关系的人。四是国家本身,与荣誉、称颂与知名度一起,经常取代父母的位置。最后是财产,包括法律让我们支配,以及我们有权出售或放弃的任何东西。
奥古斯丁的这一思想特别值得我们注意。这些内容和后来自然法的三大原则非常接近:自我保存、繁衍后代、过社会生活。更让人惊奇的是,这一思想非常近似于近代社会契约论观点:人的天赋权利就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他虽然强调,永恒法要求我们抛弃属世之事,朝向永恒之事,从而纯净我们的爱,但当人的贪念执著于那暂时可被称作“我们的”东西时,奥古斯丁充分认识到世俗法的正当性范围。
奥古斯丁一再强调,世俗法之所以有正当性,是因为它来自上帝的永恒法,因而他特别强调人对世俗之物的正确态度,但凡做了贪欲之奴隶的人,都起因于对世俗之物的态度出现了问题。“同样的东西,为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使用,有的用得好,有的用得坏。”“自身不善的人”,可以紧盯着善却不知道善用,本来,世俗物是奴隶,他是主人,但因为错用,他自己反倒是物的奴隶了。物本身不是恶,或者是中立的,恶来自意志选择,选择背离最高的善——上帝和永恒之事,趋向世俗之物和可变之事,恶行就产生了。奥古斯丁始终强调意志从共同的不变之善转向自己的善(私善)或一切可变的其他善或低等善,这一运动的原因不在物(或善物),仍在于意志和意志的自由选择(决断)。奥古斯丁在《论自由决断》第三卷中集中阐明了这一点。理解这一点,对我们理解奥古斯丁的自然观和法律思想非常重要,特别是对托马斯的自然法思想的形成至关重要。



三、自然和意志的区分及其意义
奥古斯丁的《论自由决断》回答的是恶的来源问题,为上帝的正义辩护,为自由意志是善的进行论证。和所有的神义论著作一样,世界的恶、人的自由和上帝的正义,是一个三而一的问题。在该书的第三卷第一章,奥古斯丁具体论证了意志离开上帝的运动是如何产生的问题,这个问题和本文的主旨———奥古斯丁的自然观与法律思想有内在关联。
奥古斯丁指出,上帝赐予我们自由意志,是为了我们能正当地生活,自由意志是善的。可是由于意志出现了从不变的公共之善向可变的低级之善的转向,这一运动是否可以指责,就在于这一运动究竟是自然的,是本性使然的必然运动,还是相反,是意志的自由选择(决断)。这里的问题关涉到上帝的意志、人的意志、上帝的恩典、自然和本性等概念。关键是自然的运动(本性行为)和出于意志的运动(自愿行为)的区别。这是奥古斯丁自由观的根本意义所在,也是其自然观和永恒法思想的精髓,正确理解这一点,对理解托马斯自然法思想的形成有直接的帮助。
奥古斯丁说:“若运动由本性或必然引起,就绝不会是可指责的。”既然这一运动是可指责的,那就说明,这一运动肯定不是心灵的自然(本性的必然)运动,而是其非本性的(非自然的、非必然的)运动,运动的动因或决定根据就是意志本身和意志的自由选择(决断)。为了说明这一点,奥古斯丁使用了一个有趣的类比:石头的自然运动和灵魂的意志运动。
石头因自身重量下落到地面,这种运动就是石头的自然运动,它非因外力作用使然,而是石头内在的重力导致的下落,这是自然运动最典型的例子,自然运动即自身运动。但人和人的灵魂的行动(运动)则不同。奥古斯丁一边总结一边回答埃乌迪乌斯时说:“我们一致认为,只有心灵自己的意志才能使它成为贪欲的奴隶。优越于它的或与它平等的,不可能强迫它那样,因那是不义,而低于它的也不可能强迫它,因那是不可能的。只剩下一种可能,即意志从喜爱造物主转向喜爱其造物这一运动属于意志本身。所以,说那运动该受指责——你说过怀疑这点乃是荒谬的——那它不是自然的,而是志愿的(voluntarius)。”
意志的堕落运动,其主体是意志,石头的下落运动,主体是石头,看上去相似,但实质完全不同。因为,石头自身无力阻止自己的重力而下落,但意志却有能力改变其意愿。意志只有在自己意愿如此堕落下沉时,才可以抛弃更高的事物,而喜爱更低的事物。所以,石头运动是自然而然的,是必然运动,但灵魂的运动是志愿的。正因为它是志愿的,才是可以指责的。另外,上帝恩典人意志,是为了人能正当行为和生活,遵循上帝的意志行事,遵循永恒法,这是自然的秩序,意志出于自己的意愿选择背离最高的善,趋向更低级的善,则是意志的自由决断,这是意志的志愿行为,因此必须承担受罚的责。奥古斯丁在卷二中指出,这种运动的原因绝不会从上帝而来。
人的意志来自上帝的意志,来自恩典,但恩典并不表明,人作为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作品,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出自己的决断(选择),这种选择不是自然的必然行为,而是志愿的行为。意志的自由决断是理解奥古斯丁自然观和自然法(永恒法)思想的利器。奥古斯丁自然观对希腊自然概念的最大改造,不是在于强调作为实体的自然和上帝的(本质)之间的必然联系,而恰恰在于,他强调了本性(自然)行为和志愿行为的区别。关于世俗法和永恒法的区别,他的思想意义也恰恰在于阐明一个道理:人的意志和上帝的意志之间存在着绝对差异,但是人的意志有可能选择遵循永恒法,远离世俗法,也可能选择按照世俗法行为,违背上帝的永恒法,但无论如何,自由选择是人的意志活动,而非自然的必然活动。
奥古斯丁关于自然的论述,关于永恒法与世俗法的区分,直接影响了托马斯的自然法思想。
在奥古斯丁那里,自然来自上帝,法来自上帝的意志,因此法在本质上是永恒的,这体现了世界的客观秩序,人的生存只能遵循这一永恒而客观的法的秩序,才有幸福和善生。但在托马斯那里,自然不仅来自上帝,而且和理性密不可分,理性与自然几乎就是同义语,自然是理性的本性,自然即本性,自然法即本性法则。然则,托马斯的法哲学思想不仅表明其思想对于奥古斯丁的改造,更反映出其内在的逻辑发展,从永恒法到自然法的发展,就是从上帝意志到人类理性的发展。纵观托马斯的思想,恩典、本性与自然法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张力关系。他的名言“恩典并不消灭本性,而是成全本性”集中表明了这一点。
托马斯所处的13世纪已经与奥古斯丁生活的时代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随着自然的理性化,托马斯尽管还言及神恩对本性的成全,但毕竟他已经开辟了自然理性的地盘,甚至可以提出“自然的自律”(理性的自治)这一主张。上帝把自己的持久与可实现能力归于自然。理性的任务就是研究自然的诸原则,解释其现象。自然物的秩序,不是理性的作品,而仅仅是理性探究的对象(Ratio non facit, sed solum considerat)。自然和理性灵魂同一,理性的第二秩序就是灵魂的第二自然。遵循自然倾向发生的事,就是自然的,遵循意志倾向发生的事,也就是意志的。意志的选择(自由决断)不仅扎根于意志及其主体之中,也扎根于理性及其根据中。
奥古斯丁的自然观以及对世俗法和永恒法的区分,与其说对托马斯自然法思想(法哲学总体)产生了深刻影响,还不如说直接影响到托马斯的永恒法思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自己对奥古斯丁的频繁引用看得出来。在《论法律》一书中,托马斯在论述永恒法和自然法的部分,频繁引用的两大人物就是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丁。对托马斯产生重要影响的绝非亚里士多德一个人,更重要更直接影响他的是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论证法律时几乎不讲自然法,他论证的是永恒法与人法(世俗法)。自然法论题是缺席的。而托马斯在讨论自然法是否就存在于我们内部时,他首先提出一个反论就是以奥古斯丁为例。他说:“我们之内似乎不存在自然法。因为人有永恒法的统治就足够了,正如奥古斯丁所言,借助永恒法所有事物都得到了最有秩序的安排。”托马斯也说,只需自然法,一切人间秩序就可以得到最好安排,似乎不需要人法或世俗法了。他再次援引奥古斯丁的话说:“永恒法概念铭刻在我们心中。”托马斯在问题九十三部分论述永恒法时虽然强调他探究法律的方法是,通过法律自身,通过其效果进行推论,与奥古斯丁先验的抽象方法不同,但他应用奥古斯丁的文献绝不止于《论自由决断》,还有《论真宗教》《上帝之城》等等都在他的援引范围。比如前面所引用的奥古斯丁那句“永恒法铭刻在我们心中”,在《忏悔录》里也出现过,被托马斯引用,表明奥古斯丁其实也有自然法思想,因为在心中的法就是自然法。“但是相反,奥古斯丁说‘你的法律铭刻在人心中,这是不义无法抹去的。’但铭刻在人心中的法律是自然法,因此自然法无法被抹去。”
与奥古斯丁在其法理论中强调人的意志,弱化本性(自然),突出上帝恩典的倾向形成对照,托马斯在其法哲学中比较强调的是人的理性和自然,而非上帝的恩典和意志。托马斯说:“虽然恩典比自然更有效力,但与恩典相比,自然对人更根本,也因此更为持久。”
虽然托马斯在其论证中,经常以奥古斯丁为反论代表,自己常常在驳斥中给出自己的回答,但他关于永恒法与自然法的思想,大部分来自奥古斯丁关于永恒法的论述,这可以从他的《论法律》一书中清楚地看到。没有奥古斯丁关于永恒法与人法的区分,托马斯的永恒法思想就会苍白甚至空虚,尽管其自然法理论和习性思想更多来自亚里士多德。
总之,奥古斯丁虽没有成熟的自然法理论,但他对永恒法与世俗法的区分仍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区分不仅对古典自然法思想是一次革命性转换,更对托马斯自然法思想产生了奠基性意义。
本文发表于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6期
注释、参考文献从略
作者简介
张荣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领域:中世纪哲学,德国近现代哲学,
基督教哲学,生命哲学与伦理学。
编辑 / 唐铱涵
校对 / 刘雨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