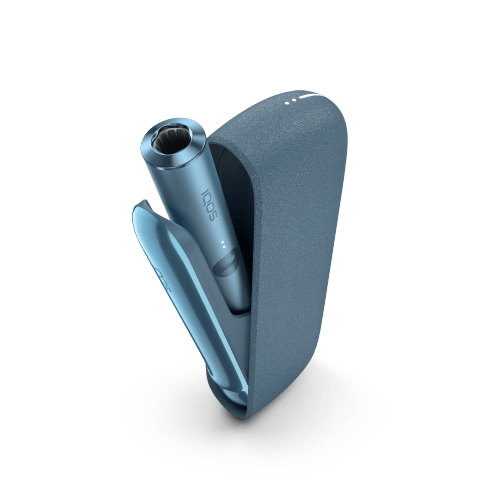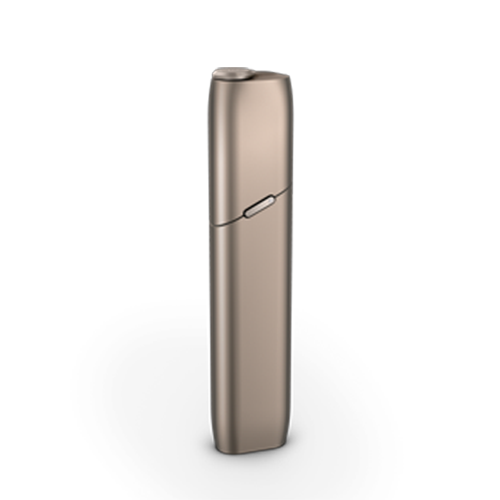尼采的影响
尼采的影响

卡西尔在一篇评论康德的文章中说过,伟大思想家的周围总是笼罩着一层浓厚的晕圈,但这一晕圈不仅没有折射,反倒愈加掩盖了思想家自身的光芒。这一说法适用于康德更适用于尼采。尼采曾把自己比作时代的“继儿”和“坏良心”,他认为自己的时代远远没有到来,而是属于“明天之后”。不过多少显得有些反讽意味的是,这位生前自以为“不合时宜”的哲学家在死后不久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最终主宰了此后一个多世纪西方思想的整体格局和走向。20世纪的西方哲学、神学、文学、艺术、社会科学、历史学和心理学等,无一不打上了尼采的烙印。各种各样的思想流派,譬如存在主义、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精神分析、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直至今天方兴未艾的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和东方主义等,都一致把尼采奉为鼻祖。那些在立场上极端分歧甚至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如左翼激进主义、右翼保守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也都毫无例外地援引尼采为各自的代言人。更有形形色色的“哲学工作者”、学者、诗人、艺术家、神秘主义者、革命家、无神论者、狂热分子、宗教徒等,如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四卷中的“高人”一样以尼采的门徒自居,纷纷宣称从他那里获得了真正的灵感和神秘的启示。所有这些都如同“一层浓厚的晕圈”把尼采笼罩得严严实实,以至于他真正面目反倒日益模糊,不复能够辨认。
尼采当然预感到了自己在未来时代的这一命运,否则他也不会在《瞧,这个人!》反复强调,不要把他同任何他人相混淆。尼采之所以反对柏拉图主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防止任何人把他理解为柏拉图主义式的“著名智者”——尼采从来就无意制造一个“尼采主义”的传统,更不想鼓吹某种“民众的尼采主义”,所以他才尤其强调,“每一位深刻的思想与其说是害怕被人误解,不如说是更害怕被人理解。”(《超善恶》,格言290)不过尼采当然知道,由于哲学家的思想和生活“节奏”与其他人存在着巨大反差,由于他们在视角上截然对立,作为“隐微者”的哲学家在其他人眼里却成为一位“显白者”,他所显示于人的“显白视角”也成为掩盖甚至遮蔽自己“隐微视角”的重重“面具”,以至于他的哲学作为一个“文本”反倒最终变成了一个层层叠叠的“解释”史或效果史。这既是柏拉图哲学的命运,也是尼采哲学的命运。所以,倘若把尼采的解释史或影响史也视为其哲学的一部分,那么如何根据20世纪的尼采解释史来重新审视他的基本问题,则显得尤为必要。
尼采曾把哲学家比作“文化的医师”。用美国学者丹豪瑟的话说,“他的哲学既是对其同时代即19世纪的疾病或危机的诊断,也是对治疗方法的探索。”从早期的《悲剧的诞生》、《真理和谎言之非道德论》和《历史对生命的用途和滥用》,到中期的《曙光》、《快乐的科学》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直至后期的《超善恶》和《论道德的谱系》等,尼采一生的哲学思考正是这样一种“医师”式的实践。不过他的诊断和治疗范围决不仅仅局限于“19世纪的病症或危机”,因为在他看来,19世纪的虚无主义危机——“上帝死了——并不单纯是一个19世纪的现象,而是体现了两千多年西方文明本身的总体危机。事实上,当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 (西塞罗语)、当柏拉图紧接着发明了一套柏拉图主义的神话时,西方文明的危机就已经开始了。此后漫长的两千多年历史,不过是一个西方文明不断地自我颠覆和自我毁灭的“错误历史”。
尼采对柏拉图主义历史的病理学诊断,必然包含了他对西方文明的整体理解。在尼采的心目中,西方文明在有史可载的开端就已经不可思议地达到了自己的顶峰,这就是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希腊文明。希腊文明的伟大成就体现在两个方 面,其一是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哲学,其二是希腊悲剧。前者使希腊人走出了荷马及赫西俄德的原始神话世界,开始以清醒的眼光观察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宇宙,并且洞察了“万物流转、无物常驻”的“真理”。但是,希腊人并没有因为对“生命无常”的深刻体悟否定了生命本身的意义;恰恰相反他们创造出了一个“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的悲剧世界,一个“梦”与“醉”的“幻象”世界;正是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他们遗忘了“生命无常”的“现实”,并且以巨大的热情从事政治、战争、艺术、体育等活动。
在尼采看来,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希腊文明之所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是因为它很好地维持了哲学与悲剧或宗教之间的平衡或张力:一方面,以泰勒斯、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里特等为代表的自然哲学家虽然走出了神话的世界,但却很好地节制了自己的“知识冲动”,从而为希腊悲剧的创造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他们始终保持了清醒的求真意志,从来不为作为民众偏见化身的希腊悲剧所左右。但是,苏格拉底改变了这一切。出于对希腊人高贵信念的敌视,苏格拉底用冷酷的辩证法摧毁了希腊悲剧,并且用一套理性主义或功利主义的道德说教取而代之。在他的巨大诱惑下,柏拉图—这位古代世界最高贵的精神类型——用整整一生的时间来为这套道德说教进行辩护,把它从一个“民众话题和俚俗民歌”神化为“至善”或永恒真理,最终“把它变成了无限和不可能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柏拉图主义,是“迄今为止的一切错误中最糟糕、最漫长和最危险的错误”。
对比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希腊文明,柏拉图主义的最大错误正是在于颠倒了哲学与民众偏见之间的关系。为了安抚民众对“生命无常”的恐惧,柏拉图主义不惜编造了“德性就是幸福”、“灵魂不朽”和“善恶报应”之类的道德谎言,由此放弃了哲学统治民众偏见的特权,并且在根本上败坏了作为求真意志的哲学生活本身。不仅如此,柏拉图主义的更大危险是为基督教铺平了道路,因为后者进一步用一个子虚乌有的超验上帝否定了有限生命或尘世,从而使柏拉图最初所要捍卫的等级秩序变得既不可能(因为一切不平等的生命在上帝面前都一律平等),也无必要(因为一切有限的生命相对于上帝都没有任何意义)。
基督教把柏拉图主义变成了“民众的柏拉图主义”,它对希腊和罗马文明的胜利是“奴隶道德”对“主人道德”的胜利。在尼采看来,基督教在文艺复兴和现代启蒙时期的衰落,原本是西方终结这一“错误历史”的最佳时机,但是宗教改革和现代“民主启蒙”不但摧毁了这一希望,而且把西方文明进一步推向现代虚无主义的黑暗深渊。在这样一个“人人追求平等、人人也都事实平等”的现代社会,公意(general will)取代了神意(providence ) ,“晨报取代了晨祷”。这样一种“普遍同质”的现代国家,不仅意味着两千多年的西方文明历史彻底“终结”,而且表明它已经堕落到了极点,因为西方人除了低贱的“畜群道德”和“末人”理想,除了贫乏而空洞的“权利”或“自由”之外,再也没有任何伟大的奋斗目标或生活信念。用尼采的话说,他们除了追求虚无(Wille zur Nicht ),再也无所追求(nicht will )。
不过对尼采而言,危机或许恰恰就是转机:柏拉图主义的崩溃或“上帝之死”,虽然使西方文明面临深刻的虚无主义危机,但却同时包含了克服这一危机的可能。只不过尼采非常清楚地看到,克服现代危机的途径绝对不可能是简单地返回古代,哪怕这个“古代”是他最为向往的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希腊文明。古代的诸神已经被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完全杀死,而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的超验世界或上帝也被现代科学的“理智良心”彻底否定,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单纯地返回古代的努力都是一种拙劣和卑贱的自我欺骗。既然返回古代的道路已经被堵死,那么西方文明的复兴恰恰要依靠一种面向未来的创造。对尼采来说,“复古”意味着“革命”,而“革命”才是真正的“复古”:只有彻底否定自柏拉图以来的两千多年西方文明历史,才有可能在根本上克服它所导致的现代虚无主义危机。在这个意义上,尼采对西方文明的病理学诊断就是对其内在病症或危机的治疗,而这一可能性则正是基于他对哲学的全新理解。
尼采从来没有指望能够简单地回到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希腊文明——两千多年的柏拉图主义历史使得这种“返回”已经变得既不可能,也没有任何必要。恰恰相反,他把西方文明的希望寄托给未来,寄托给未来哲学和未来哲学家。未来哲学超越迄今为止的所有哲学类型,包括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哲学,因为未来哲学家把“求真意志”或“理智诚实”贯彻到底,从而拥有最高程度的自知之明(Selbst-Erkenntnis)。说得更具体些,正因为未来哲学家深刻地洞察了“生命就是权力意志”的真理,同时也因为认识到这一洞察本身也是一种权力意志,而且是“最富精神性的权力意志”、“创世意志”或“追求第一因的意志”,他才把“真理”或“求真意志”变成对生命的最高肯定——“不仅学会顺应和容忍一切曾在和现在,而且希望如其曾在和现在地重新拥有一切曾在和现在,希望永恒地重新拥有它,永不知足地呼喊‘再来一次’。”既然“真理”是对生命的最高肯定,那么“权力意志”的未来哲学就必然孕育了“永恒轮回”的未来宗教。作为“人所能达到的最高肯定形式”,“永恒轮回”的未来宗教就是西方文明的“第一千零一个目标”。只有这样,未来哲学家才能把西方文明从两千多年的“荒谬和无意义”中解放出来,并使它重新获得它在前苏格拉底时期所爆发出来的巨大生命力。一言以蔽之,未来哲学家只有彻底摧毁柏拉图以来的两千多年西方文明传统,才能在废墟上重建真正的西方文明。
令人相当惊奇的是,尼采的结论虽然听起来颇为惊世骇俗,但在20世纪的西方思想界却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其中最有争议性、但也最有吸引力的,当然是他对西方文明的整体理解以及对现代虚无主义危机的深刻洞察。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西方思想的整体格局正是通过对尼采的不同解释才得以展开,其中最有典型意味的则是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德里达和德留兹等人的后现代主义,以及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哲学。
海德格尔很早就接触了尼采的思想,但直到30年代中期才开始真正地思考后者的基本问题。就对西方文明的整体理解而言,海德格尔同尼采几乎完全一致,他也把两千多年的西方文明看成是一个柏拉图主义或形而上学的历史。海德格尔认为,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希腊悲剧和哲学作为“存在”的最初“敞开”构成了西方文明的“第一次开端”,但随着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存在(Sein)等同于某种永恒“在场”的存在者(Seiende ),如理念或实体等,并且相应地把存在的言说(Logos)变成了一种本体论(Ontologie)或形而上学( Metaphysik ) ,“存在的遗忘”就已经开始了;随后在中世纪,基督教的神学家们把“存在”进一步等同于上帝,并且相应地把本体论变成了一种本体论--神学(Onto-Theologie ),从而加剧了“存在的遗忘”;最后到了现代性时期,人作为“主体”取代了上帝的地位,成为衡量“存在”的最高原则或终极根据,这种现代的主体性形而上学无疑是对“存在”的彻底“遗忘”,最终把西方文明推向虚无主义的危机。
但也正是因为海德格尔对西方文明及其危机持有同尼采几乎完全相同的理解,所以他才反过来对后者提出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指控:尼采虽然一生都在批判柏拉图主义或形而上学,但却导致了形而上学历史的最终实现。根据海德格尔的解释,“权力意志”的“永恒轮回”作为尼采哲学的两个方面,恰恰构成了对“存在者整体”这一形而上学基本问题的回答:前者作为“本质”( essentia)回答了“什么存在”( Was-sein),后者作为“实存”(existentia)回答了“如何存在”(DaBsein)。进而言之,当尼采把“存在”变成“价值”、把“真理”当作“权力意志”的设定时,他已经使形而上学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程度——“价值形而上学”。更重要的是,这种价值形而上学在无限地抬高人之“主体性”的同时,也把技术对自然、大地或世界的征服发展到了极至,以至于使“诸神”纷纷逃离大地,西方也陷入了对“存在”的最深“遗忘”。一言以蔽之,尼采克服虚无主义的全部努力恰恰最终把西方推向虚无主义的最黑暗深渊。
这样一来,问题似乎并不仅仅在于海德格尔是否或者在什么意义上误解了尼采的意图,而是在于:就对西方文明总体危机的治疗来说,海德格尔同尼采的根本分歧究竟何在?尼采终生都以一位追求真理的哲学家自居,他同柏拉图等西方历史上的伟大哲学家一样坚信,哲学构成了西方文明的真正基础和精神顶峰,相应地哲学家对这个文明的健康成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尼采而言,柏拉图主义或形而上学的终结非但不是哲学本身的终结,反而使真正的未来哲学成为可能。尼采之所以彻底否定自柏拉图以来的整个西方哲学传统,是因为他要在根本上为西方文明奠定新的哲学根基。这也意味着,尼采既没有否定哲学,也没有放弃通过哲学来重建西方文明的信心。
但在一个哲学家的“德性”和历史的“命运”之间,海德格尔选择了后者。对他来说,西方文明在前苏格拉底时期的“第一次开端”——作为一个“重大事件”( Ereignis )——完全属于“存在”自身的神秘启示,此后的“存在之遗忘”也不是哪个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或尼采等)有意为之,而是同样属于存在的“天命”或“馈赠”。现代虚无主义的命运不过意味着,西方文明已经彻底耗尽了“第一次开端”的全部可能性与生命力。至于“第二次开端”或“存在”的再次“敞开”,西方只能耐心地等待。不过海德格尔明确地表示,西方文明的“第二次开端”不仅与“哲学”无关,甚至与“西方”无关,因为哲学作为第一次开端的可能性已经彻底“终结”了,而西方也必须开始学会从非哲学的东方寻找自己的转机。
后现代主义者完全继承了尼采和海德格尔对柏拉图主义或形而上学的批判,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如果说尼采把西方两千多年的形而上学看成是一个“错误的历史”,海德格尔认为它是“存在的遗忘”,那么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达则将其视为一种根深蒂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根据德里达的解释,自柏拉图以降的西方形而上学家无不偏执地追求某种“同一性”,譬如真理、上帝或主体等,并且以此来统一、整合甚至消除“差异性”;由此,凡是合乎理性或逻各斯(Logos) 的因素就居于“中心”地位,凡是不符合“逻各斯”的因素——如神话、诗歌、隐喻等——都遭到排除和否定,从而被放逐到“边缘”。但是德里达提醒说,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本身却是一个“隐喻”。因为就连柏拉图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至善”或“真理”无法用理性的语言或逻各斯来表达,而是只能将其比喻为“太阳”。在他之后,太阳的比喻一直贯穿了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譬如基督教神学家用它来描述上帝(奥古斯丁),近代哲学家用它代表人的意识或心灵(笛卡尔)。一旦表明西方形而上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也是一个隐喻,那么它所预设的“同一性/差异性”之二元对立就立刻土崩瓦解——“边缘”颠覆了“中心”,“差异性”最终取代了“同一性”。
从精神实质上来说,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同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历史的拆解(Destruktion)当然是一脉相承,他对“差异性”的强调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后者的“存在论差异”之启发。但也恰恰因为如此,德里达反过来批评海德格尔的不彻底性。在他看来,海德格尔虽然声称放弃了对“在场”的形而上学追求,但却仍然希望追寻“存在”隐退之后所留下的“痕迹”,所以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形而上学的影响。由是观之,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颠覆反而不如尼采那么彻底。德里达之所以完全不同意海德格尔对尼采的评价,如“颠倒的柏拉图主义者”、“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 “虚无主义的完成者”等,是因为他把尼采的“哲学”本身看成是一种彻底的“解构”实践。换句话说,尼采根本没有建立什么“价值形而上学”,他的所有思考都是一个反形而上学的思想实验和语言游戏。用德里达本人的话来说,尼采的全部文字都不过是“能指”符号的无限“分延”。所以,尼采最大程度地解放了“差异性”或“不确定性”,却从不追求什么“同一性”或“确定性”。
德里达对尼采的这一看法,在相当大程度上代表了后现代主义者的共识。譬如福柯也强调说,尼采同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一道彻底颠覆了西方传统的、尤其是16世纪以来所形成的解释技艺,从而使任何寻找“主体”、“本质”或“真理”的解释学努力变得再也不可能,因为“没什么绝对的解释项有待解释,因为实际上,一切都已经是解释,每个符号就其本身来说并不是需要解释的事物,而是其他符号的解释”。
而德留兹则进一步指出,尼采的革命要比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更为激进。原因在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或许真的代表着我们现代文化的开端,但尼采却全然不同:他代表着反文化的开端。”所谓“反文化”恰恰代表了一种“游牧思想”。在德留兹看来,尼采之前的西方思想家在对传统思想进行颠覆或“解码”之后,总是无法摆脱“再编码”的形而上学诱惑,重新编织了一个又一个符码(code)系统;但是,“尼采是惟一无意再编码的思想家”,作为一个永恒的“游牧者”,他听任欲望或“力”无限地漂流和迁徙,但却永远不会成为重新编码的定居者。
但经过后现代主义的过滤,尼采思想中的所有肯定或建构因素都消失殆尽,只剩下无穷无尽的否定、“解构”或“价值重估”。譬如说,尼采不再是等级秩序的捍卫者,而是成为肯为一切“边缘””或“差异性”的左翼思想家;不再是西方文明的重建者,而是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一切文明的颠覆者;甚至不再是追求真理的哲学家,而是一位风格奇特的文学探险家。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后现代主义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影响逐渐扩大,尼采进一步成为形形色色的价值相对主义、平等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的代言人,以至于在女权主义者和东方主义者心目中,俨然成了反男权中心主义和反西方中心主义的象征,似乎一切遭到“中心”压制的“边缘”、一切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的““被欺凌和被侮辱者”,都可以在尼采那里获得肯定、安慰和拯救。
正因为如此,后现代主义的尼采解释遭到了施特劳斯学派的强烈挑战。不仅如此,他们还试图进一步把尼采从海德格尔的阴影中解放出来,恢复他作为一位“柏拉图式政治哲学家”的真正面目。不过施特劳斯学派的所有这些努力只有一个目的,亦即无非是要最终把柏拉图从尼采、海德格尔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中“拯救”出来。就施特劳斯本人而言,他当然完全同意尼采与海德格尔(甚至包括后现代主义者)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但他却进一步认为,他们所批判的形而上学或柏拉图主义其实同柏拉图本人毫不相干,而是中世纪新柏拉图主义者和基督教神学家的创造;事实上,柏拉图并不是一位形而上学家,而是一位“哲学家--立法者”,或者用施特劳斯本人的话说,一位“政治性的哲学家”。正因为如此,施特劳斯在反对尼采对柏拉图之批判的同时,也为他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辩护:尼采不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形而上学家”,而是一位柏拉图式的“哲学家--立法者”。
同尼采与海德格尔一样,施特劳斯的柏拉图解释也是以对西方文明之危机的深刻洞察为出发点。在他看来,西方文明的危机恰恰集中体现为现代性本身的危机:当马基雅维里等现代性的先驱宣告与古代决裂时,西方文明就开始踏上了自我毁灭的不归路,因为在一次比一次激烈的反传统革命之中,西方人一步步地放弃了对德性和美好生活的理论探究和实践追求,最终完全丧失了判断善恶、是非对错的标准。施特劳斯很早就意识到,克服现代性危机的惟一途径就是返回古代;但他同样非常清楚的是,在尼采对形而上学的毁灭性批判之后,以形而上学的方式返回古代传统已经变得完全不可能。经过漫长而艰难的探索,施特劳斯终于从阿尔-法拉比、迈蒙尼德、阿威洛伊等伊斯兰和犹太哲学家那里发现了另一个“隐微”的传统,这就是“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 platonic political philosophy )。
根据这一理解,施特劳斯回应了尼采和海德格尔对柏拉图的批判:事实上,柏拉图(或苏格拉底)同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哲学家一样把哲学看成是一种“符合自然”的最高生活方式,但出于对自己同胞的关怀,哲学家不惜返回到城邦或“洞穴”之中为他们立法,并且捍卫政治生活的权威或公共秩序(nomos );因此,与柏拉图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非但没有使哲学迎合“民众偏见”或政治需要,反而尤其强调要在哲学与政治之间保持健康的平衡和必要的张力。
施特劳斯进而认为,西方文明正是在哲学与礼法(law/ nomos )、理性与启示、哲学与诗或雅典与耶路撒冷的紧张冲突之中,焕发出源源不断的生机,而它的根本危机也恰恰在于这一冲突的完全消解。就此而言,基督教调和理性与启示的努力已经为西方文明的危机埋下了祸根,而现代性只不过是这一危机的总爆发。现代哲学家一方面宣称要用哲学来启蒙民众、消除他们的偏见或迷信,另一方面却又把哲学降低为一种维持政治社会长治久安的公民宗教,这一点恰好表明,“政治的哲学化”必然导致“哲学的政治化”。因此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性的全部危机就在于哲学和政治两败俱伤:它使西方人不仅在政治实践中丧失了判断善恶、是非对错的能力,而且也无法在理论上对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进行哲学追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施特劳斯认为西方文明的危机首先是现代性的危机,而现代性的危机归根到底意味着政治哲学本身的危机。
基于对柏拉图的这种政治哲学式理解,施特劳斯不仅拒绝了尼采与海德格尔对西方文明及其危机的诊断,而且明确地否定了他们的治疗方案。在他看来,西方文明的危机与其说是应该归咎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不如说是应该归咎于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遗忘;相应地,克服这一危机的途径也不是返回到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哲学或“悲剧哲学”,而是应该返回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奠定的“政治哲学”。不仅如此,施特劳斯还依据“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反过来对尼采和海德格尔进行了深刻批判: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虽然怀着克服虚无主义的高贵动机,试图以返回前苏格拉底之古代的方式来批判现代性,但却恰恰推动了现代性的“第三次浪潮”, 并且把西方文明推向极端历史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黑暗深渊,所以他们必须在一定的程度上为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灾难负责。从政治哲学上来看,尼采与海德格尔的共同错误都是在于,他们同此前的现代性思想家一样,完全消解了哲学与政治或雅典与耶路撒冷之间的张力:尼采希望以超人来化解哲学与诗(宗教)的永恒冲突,消除“沉思”与“行动”或“自然”与“创造”的界限,海德格尔则完全放弃了对“自然”的哲学思考或理论探究,转而诉诸某种神秘的“决断”、启示或命运。这一点恰好表明,他们仍然停留在基督教甚至《圣经》的视野之中,并没有真正地理解古代哲学的真正精神。
在尼采的众多解释者之中,似乎只有施特劳斯最有资格成为尼采心目中的“自由精神”。施特劳斯完全洞悉了尼采的意图:他把哲学看成是最高的生活方式,他承认自然等级秩序的正当性,他知道哲学不应该迎合“民众偏见”,他也清楚“隐微”与“显白”的区分,他甚至欣赏尼采作为哲学家的极度清醒与极度疯狂。然而,施特劳斯毕竟没有成为一位尼采所期望的未来哲学家。姑且不论施特劳斯对尼采的公开批评是否符合后者的自我理解,但他的确没有像尼采那样公开地赞扬“理智的诚实”。这样一来,施特劳斯就不免陷入了某种程度的困境:一方面他的“自然正确”( right by nature)必然承诺了某种柏拉图主义式的自然等级秩序,另一方面他也非常清楚地看到,作为这种秩序之基础的古代目的论和宇宙论已经被现代科学完全摧毁。施特劳斯完全洞察了虚无主义这一“致命的真理”,但他却没有像尼采那样把它变成一个对有限生命的无限肯定和祝福,而是徒劳地宣扬那个早已死去、再也没有任何人相信的柏拉图主义谎言世界。况且,施特劳斯虽然比任何人都清楚尼采的意图,但在公开的文字中却比海德格尔更不公正地贬低了尼采的意义,似乎尼采反柏拉图主义的全部努力并不是为了复兴西方文明的生命,而是仅仅导致现代性的“第三次浪潮”。
尼采生活在19世纪晚期。他仅仅预见了西方虚无主义的来临,却没有亲眼看到这一危机如何最终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在他死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西方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衰,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意识形态冷战,经历了从现代性向“后现代”的重大转向。从根本上讲,海德格尔、后现代主义和施特劳斯学派对尼采哲学的解释,恰恰体现了20世纪西方文明对自身危机的深刻反省。所以,尽管他们并没有完全接受尼采的诊断的治疗,但却在不同的意义上深化了尼采的思考。更重要的是,随着西方文明的进一步扩张,它也把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所有非西方文明都卷入到自身的危机中。在上个世纪初,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打倒孔家店”的喧嚣声中,尼采的思想同西方形形色色的现代话语一道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从而引发了五千年华夏文明之“亘古未有的大变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以一种新的眼光来重新考察尼采以及他对柏拉图以来两千多年的西方文明之理解,同时借此来思考中国文明自身的问题,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